合唱团
作者:肖楚舟
08-20·阅读时长13分钟

你想听一场合唱音乐会吗?
8月17日,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下称“彩虹”)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这个来自上海的合唱团来北京演出的次数不算多,上次已经是三年前。1500张门票,票价180~980元,发售当日一抢而空。直到演出前夕,社交平台还能刷到蹲回流票掉落的帖子,没买到票的网友盯着售票网站上密密麻麻的座位表,祈祷那些灰色的小圆点突然变红。
北京的暴雨天,音乐厅近乎满座。一个娇嫩的女声配音的“字幕机”开始报幕,熟悉彩虹的观众都知道,这是次次都有、次次不重样的彩虹式欢迎仪式。台词里点名了几位虚构的观众,个个符合北京人的形象,“为了彩虹提早结束加班的金小酒”“喜迎退休的丰台区观众黄文胜”“海淀区大学生李定国”,每念出一句话,都有一群人露出对号入座的笑容,拍红了双手。
你很难在音乐厅看到如此混乱的场面。指挥在台上喋喋不休,团员一会儿演情景剧,一会儿念诗,一会儿跳舞,观众不争气地抹眼泪或者情不自禁地扭动身体。指挥金承志邀请所有人进入他们的世界,在每首歌的开头进行一段介绍,通常与自己的生活和感受相关,具体到当时的场景,天气与心情。接近尾声,团歌《彩虹》响起,“我走过许多地方,也一直四处张望,我不停流浪流浪。春的花,夏的雨,彩虹在天上”。金承志转过身,邀请观众合唱,所有人心照不宣举起手机,点亮一片摇曳的星海。这大概是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唯一开满闪光灯的时刻。
和2016年相比,彩虹合唱团带来的横空出世式的惊喜已经过去。那一年,全国年轻人都在问张士超你究竟把金承志的钥匙藏在哪里了,华东师大的姑娘究竟有多好看,卡祖笛到底是什么东西。“合唱原来还可以这么唱”,背后是一种打破框架的惊喜。如今,合唱可以这么唱已经成为共识,彩虹成为一种标杆和模板,合唱团也有了能够支撑独立运营的商业模式,更多像彩虹一样的合唱团冒了出来。这背后是一群认可合唱、主动走近合唱的观众。

如果说在彩虹之前,合唱是“群众歌咏运动”,是大学里人人必须参加的“一·二九合唱”或者单位组织的年会表演,是一种制式化、工具化的文艺活动。现在,合唱变了。它可以不必为集体的目标服务,不再只用于歌颂与赞美宏大的事物。齐声高歌不再是乏味的形式主义,它可以表现颠覆性的狂欢,带来共振式的感动,那辉煌的和声,可以用来衬托每个平凡人的情感。
彩虹合唱团团长许诗雨对彩虹的受众做过调研,“跨度很广,难以概括。我们的观众从十几岁开始,毕竟可以进入音乐厅的观众年龄不小于12岁,还有80多岁的。这里面既有非常资深的音乐爱好者,有过合唱经历的人,还有些人可能完全没进过音乐厅,但是因为对彩虹有些兴趣,也来感受一下”。许诗雨甚至遇到过两位80多岁的老太太,她们特地从安徽坐火车到上海看演出,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向往朴素的情感和美好的生活”。
2022年,分析机构Social Beta统计过彩虹唱过的广告曲,广告商对彩虹的偏爱,折射出彩虹的受众范围之广。他们给洗涤剂品牌唱过《为什么洗碗的总是我》,给新手父母唱过《全员舒适》,给雪糕唱过《开始开心吧!》,给汽车品牌唱改编版的《敬自己心中的天籁》。广告商看中的是彩虹那种“优雅吐槽”的能力,他们总能击中年轻人最狼狈的瞬间,又丝滑地托住他们失落的心。
彩虹的起点是一个音乐学院学生的“兴趣小组”,它意味着自发、独立和自由的表达。如今,类似的合唱团已经不在少数,在全国各地涌现,出现在网络、音乐厅、音乐节、咖啡厅、公园、街头,任何可以放声歌唱的地方。用戏谑消解庄严,用恢宏衬托渺小,年轻人开始加入自发组成的业余合唱团,唱自己爱讲的故事。

人为什么要一起唱歌?
在听完彩虹第一次排练后的一个晚上,我给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王瑾打了一个跨洋电话。这个暑假,她正领着自己的业余合唱团,在西班牙参加国际合唱节。王瑾指导过许多上海的高校合唱团、业余合唱团,是上海音乐家协会合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她在2005年成立了百格合唱团,一个由各行各业白领组成的业余合唱团。金承志和他的许多伙伴们,都是王瑾熟悉的后辈。合唱不是中国原生的表演形式,起步比较晚,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宣传性、工具性大于艺术性的状态。民间的业余合唱团真正发展起来是在2000年之后,用王瑾的话来说,“到现在还是一个新生的阶段”。
我问王瑾,从音乐性上讲,合唱这种艺术形式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对我讲起第一次被和声的力量打动的场景。1997年底,中国合唱指挥家吴灵芬到中国音乐学院开设了合唱指挥课程,王瑾那时还是学生,选修了这门课,“我到得比较晚,在排练室门口听到有200人的和声共鸣,听得我起了鸡皮疙瘩。我从小到大学习音乐,在一个耳熟能详的环境里,突然听到和声的共融度,突然就迷上了。跟乐队合奏不同,合唱不是间接地通过乐器来传达情感,而是通过声音形成最直接的表达。”
1998年,两位合唱指挥,来自英国的科林杜兰特(Colin Durrant)和来自希腊的埃万杰洛斯希莫尼德斯(Evangelos Himonides)合作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人要一起唱歌?》。他们发现,尽管形式上存在差异,一起唱歌的需求却广泛存在于人类生活中,他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篇文章涵盖了心理学、社会学、跨文化研究的文献,还包括对一个合唱团的田野调查,最后,两位作者认为:为什么人们需要在其他人中唱歌?种种结论仍然非常不科学,答案可能难以令人信服。唯一可能得到答案的方法就是回到音乐的力量本身,“集体歌唱体验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它的满足感如此深刻,以至于那些分享过这种体验的人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与音乐的关系。对于这样的人来说,音乐不可避免地成为生活中最深刻的回报之一。鉴于对这种满足的普遍需求以及它在人类生活中的稀缺性,这绝非小事。”
英国音乐家朱利安约翰逊(Julian Johnson)在讨论合唱的起源时,提到了16世纪以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为中心发展的竞奏风格(concertato style)。从这里开始,大型合唱开始不止服务于宗教目的,还传达世俗情感。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它为何在威尼斯出现?朱利安的结论是,威尼斯作为当时世界商业文化中心,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各阶层和谐共处的社会秩序,这种结合了声乐与器乐,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组合音乐,其实象征着各阶层紧密协作而充满凝聚力的理想社会。“对听众来说,通过音乐来理解这种秩序感并不困难。因为这些复合唱作品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对比效果,会给人一种直击心灵的冲击与震撼。”
据王瑾观察,中国的合唱整体上一直是“两头多中间少”的分布,老年合唱团和少儿合唱团多,成年人的业余合唱团少,“这是可以理解的,30岁到50岁的成年人生活里要解决的议题太多,时间和精力难以分配”。但近几年,她也观察到“中间”的合唱团正在增长,中青年群体开始顶着日常生活的繁重压力,被合唱团吸引,“大家对合唱的认知也变得多元化,受众似乎也变多了,合唱作曲家也逐渐增多,这在20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王瑾觉得背后的原因是多样的。一方面是,国内第一代有条件从小参加合唱团的孩子长大了,他们还想要继续这种群体生活。另一方面,一批有想法的年轻人的合唱实践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金承志,改变了合唱的话语,“他会在合唱作品中使用年轻人的想法和词汇,打动了年轻人,说出了年轻人的心理,主要是让年轻人认为这种音乐很有趣”。也改变了传播方式,“打破了原来的边界,尤其是利用网络打破了合唱的场所边界,也在内容上改变了合唱的内容边界。在年轻人中传播很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他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很难找出一个从没参加过合唱团的中国人。即使是那些对艺术最不感冒的人,也必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参与过一场集体合唱活动。过去的印象里,合唱是集体框架下的工具性表演,和学分、业绩、领导印象分挂钩的刷脸活动。现在,当合唱空洞的外壳被敲碎,人们发现发自内心的集体歌唱原来如此迷人。

齐格蒙·鲍曼用“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括现代人生活的不同侧面。流动的生活意味着一种不断向前奔跑的惯性,害怕被抛下成为生活的主题。这种生活充满持续不断的新开端,同时全是焦虑,没有什么是稳固的,“遗忘、删除、放弃及替代”成了生活的侧重。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不再受到固定地址、固定的人际关系体系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拘束,我们拥有了不断更新换代的产品、服务、关系、兴趣和生活方式,也不断失去赖以自我锚定的支点。昨天的同事可能是今天的路人,去年生活过的街区今年就夷为平地,我们挣扎其中,只能“无望地试图把无用的、短暂的东西变成耐用品”。在快成一片残影的生活里,合唱团的坚实与稳固反而显得珍贵而有力量。一段漂亮的和声背后,必然存在一群相互理解的人。
王瑾带过各式各样的合唱团,有校园合唱团、百格这样的白领合唱团,也有在沪外国友人组成的国际合唱团。她觉得与现在年轻人可以选择的其他社团活动相比,合唱团最大的特点是“在场”。它要求你在线下共处一室,要求你充分聆听他人,要求你懂得配合,这些可以说是“合唱人的性格”。
合唱团的稳固性惊人地持久。在王瑾看来,把合唱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人生时期找到一个特定的组织,演唱一些真正让你感受到心灵震撼的音乐。人生的轨迹会发生变化,你生活的城市会发生变化,但你总是去寻找可以合唱的地方,能够共情的音乐,一群一起唱歌的人,这一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你的生活”。
美国畅销书作家丹尼尔·平克在讨论群体管理的时机问题时,也谈到合唱带来的心理益处,它能提升自尊,减轻压力和抑郁症状,强化人的目的感和意义感,“这些效果不是来自歌唱本身,而是来自和别人一起歌唱。例如,在唱诗班中唱歌的人比独唱者的幸福感要高得多”。
平克提出一个词语总结合唱的奥义,“群体同步”。他将合唱团中的同步感与“桨手效应”类比,这个说法来自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华盛顿大学9人赛艇队的故事,“如果正确培养出这些近乎神秘的信任和情感纽带,就能让一支赛艇队超越平常的境界,达到一种九人合一的状态一种无法言说、天人合一的东西,当队员们击桨时,艰苦为狂喜所取代”。同步的感受甚至能抵消痛苦,而合唱是这种同步效应最有力的表现形式。
运动过程中的同步是肉体层面,合唱引发的同步则能够通向心灵。“合唱者们的声音当然是整齐的,任何人都能听得出。然而,他们身体内部所发生的,虽然听不见,却很重要,也很有趣。在这次演出中,这些背景各异的业余歌手的心脏将以同样的速度跳动”。那种共振感能冲破一切伪装和矫饰,让你释放出最真实的情绪。
2020年,彩虹登上了综艺节目《炙热的我们》的舞台,和摇滚乐队、偶像团体同台表演。中间有一个环节,彩虹改编了火箭少女101那首广受争议的神曲《卡路里》。团员在长桌前排排坐,面前人手一张化妆镜,金承志身穿白衬衫站在长桌边深情款款,连演带唱。躁动的节奏被拉长,把减肥少女的心事缓缓道出,有点丧又充满渴望,与方便面、甜甜圈的惜别之情在和声中上下翻飞,缠绵悱恻。金承志为这次竞演重写了几句歌词,“有时满意,有时想远远逃离,我还能怎样,我只能燃烧”,抒情的吟唱过后接下来是全员和声,“燃烧!”“燃烧!”“燃烧!”镜头一切,习惯了表情管理的偶像团体成员们哭得面目狰狞。
如果感到孤独,就来合唱吧
去年,彩虹发起了一场合唱网络活动,邀请全国各地的合唱团翻唱《声部介绍歌》,最后有效投稿达100多份。《声部介绍歌》是那种典型的在“集体中表达自我”的歌曲,有点像整活版的自我介绍,很不“合唱”。四个声部各行其是,争奇斗艳,男高务必要把自恋进行到底,男低音要挑战唱不上去的高音,低调的女中音充满好胜心,嘹亮动听的女高音有点刻薄和高傲。就连钢琴伴奏也要出来一秀歌喉,唱一个未必能平稳落地的高音抛物线。
彩虹的运营团队告诉我,他们也没料到这首歌能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更没想到全国各地有那样多、那样丰富的业余合唱团。其中高校学生自发组织的合唱团占比最大,以企业、机构为单位组成的合唱团也有不少,还有来自海外的华人业余合唱团。无论职业、年龄与场合,一起唱歌的欲望正在萌发。
谨菲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第五元素合唱团的成员,也是她带着团员参与了彩虹发起的《声部介绍歌》活动。当我们聊起彩虹的时候,她激动地报起了菜名,她喜欢早期一首不大广为人知的曲目《夕烧》,也记得热闹到掀翻屋顶的《活在爱里面!》,还有2021年彩虹专门在武汉场献唱的《道别是一件难事》。“彩虹是年轻人中最受欢迎的合唱团,谨菲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他们用心表达,而且知道如何去讲故事。”彩虹的歌曲几乎能嵌入这个年轻人生活中的每一道情感缝隙,前几天,谨菲所在的合唱团刚刚开始排练金承志写的《打转转》,这是一首婉转抒情的小曲,开头唱两个人坐着船在水面打转,最后一个上了岸,一个留在船上。谨菲觉得它很适合快毕业的心境,“他讲的是人在一段关系中的一种处境。有句话很适合概括这首歌,你去向那里,我留在此处”。
谨菲来自一个理工科院系,课业繁重,竞争激烈,大家的学业和生活安排不一定同步。学校里其他的社团有很多,大多是名义上举办一些活动,是否参加看个人意愿。总的来说,她生活在一个比较疏离的环境中。这也是当下大学生的常态,如此度过四年也无可厚非。但合唱团改变了她的想法。
她看中的恰恰是合唱团一些听起来非常古板的惯例。每年暑期,团员要花20天集训,训练期间不许使用手机,必须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一起唱歌游戏的集体生活中。有人会望而生畏,但谨菲觉得这样的经历难能可贵,“几十个人这么长时间相处,一起快快乐乐地唱歌玩耍,除了一些艺术团和体育团,这样的机会在整个学校都非常罕见。但那些是需要门槛的,合唱不用”。
线下共处、相互配合、考虑他人,这些体验说起来像是负担。为什么在家庭、学校或者职场里饱受压力的都市人,还愿意再给自己找一个这么费劲的爱好?
实践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的好处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概念由认知人类学家珍·拉夫(Jean Lave)和教育理论家爱丁纳·温格(Etienne Wenger)共同提出,简单来说,“实践社群”就是一群“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抱有共同的关注或热情,并在定期互动中学习如何做得更好的人”。
心理学家在分析合唱团的结构时,将业余合唱团定义为一个典型的实践社群。与一般的趣缘团体不同,实践社群要求你贡献知识与能力,最终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样的社区中,人们通过参与和贡献社区实践来体验或创造自己的共同身份。由于目标的存在,这里或许没有指定的“领导职位”,但是有“未经选举的领导者”。他们跟生活中分配给你的老板不同,是你主动选择信任和依赖的对象,比如一个读谱技能更熟练的团员,一位经常坐在你身边帮你校对音准的团友,或者每次排练后负责收拾凳子的热心团员。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有必须履行的承诺,集体的规则和束缚存在,但它们不再意味着不可撼动的秩序和随之而来的压力,而是信任与归属感的来源。
谨菲带着合唱团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加班加点赶出《声部介绍歌》。对于一个校园合唱团来说,这首歌并不简单,要凸显各个声部的特点,高高低低的音调都有需要“炫技”的部分,还要在每个人不同的课表中挤出排练时间。最后他们得到的“回报”也是非物质性的一份彩虹合唱团的周边礼包,被剪进活动集锦视频,以及从前毕业的老团员的热情转发。
当投稿成功,被人看见的那一刻,对这个顶着沉重的课业压力,即将面临残酷成人世界的女孩来说,一切都圆满了。她告诉我,按照惯例,升入毕业年级后她就要退出合唱团,但她总觉得自己将来还会找一个地方合唱。她喜欢《那天我一个冲动加入合唱团》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感到孤独,那么不妨找别人一起唱个呜。
合唱团有多吸引人?这期封面,我们分别前往四个城市,采访了几个合唱团,听他们唱,也和他们一起唱。我在上海沉浸式体验彩虹这个最能唱出当代年轻人精神状态的合唱团,究竟如何塑造。刘敏在成都和全男声合唱团吾恣聊了聊,讨论在艰难的世俗生活之外,为何仍然需要一块精神保留地。孙雅兰去了南宁,听翻唱《黑猫警长》走红的越人合唱团如何用南宁方言做合唱。段弄玉去了广州星弧合唱团,作为素人,尝试放声歌唱的感觉。
当合唱不再是被动参与的集体活动,不再与奖项或者绩效挂钩,合唱的本质,那种精神同步带来的归属感和稳定感,反而得以凸显其价值。升级换代后的合唱团,成为一个介于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安置场所。当你疲于交往又渴望拥抱,当你追求自我又担心孤独,当你想被听见又害怕关注,去找一个称心的合唱团,加入群体的歌唱。
(参考资料:齐格蒙·鲍曼,《流动的生活》;丹尼尔·平克,《时机管理》;Etienne Wenger,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 Brief Introduction)
文章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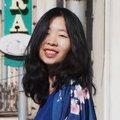

肖楚舟
发表文章0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95人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