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茎漫谈:人的百分之六十是香蕉?
作者:读书
09-06·阅读时长12分钟
文·刘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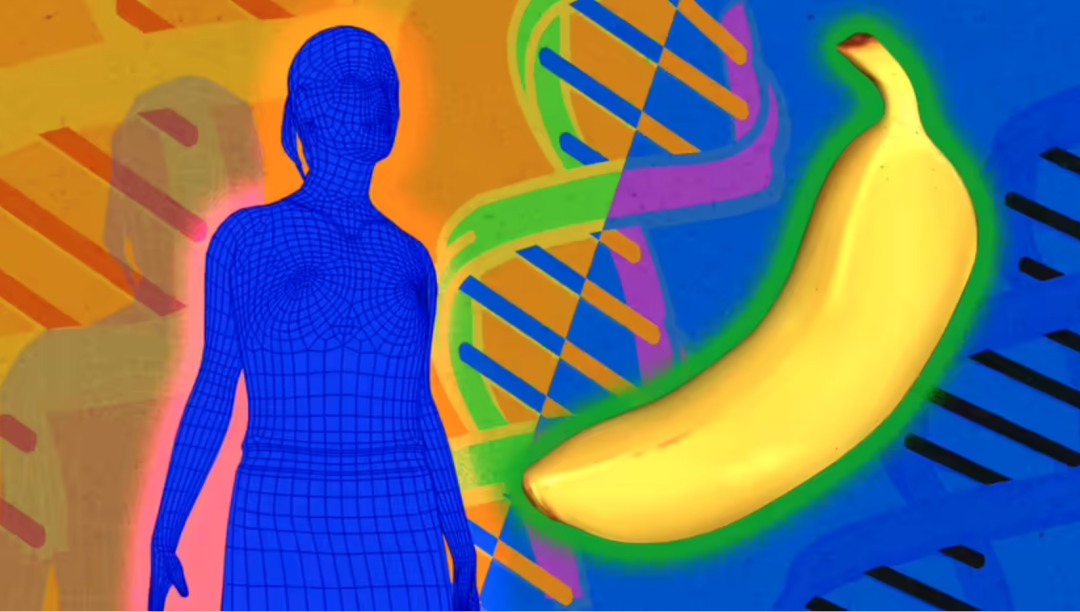
不久前,《读书》的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人在动物性之外,还有植物性吗?”
闻之,我一时诧异,动物性也好,植物性也罢,皆直指人的生物属性。然而,当下最被热议的命题恰恰不是人的生物性,而是人的非生物性,或曰,人的非生物嫁接何以可能。以人工智能的滥觞为契机,穿戴式外骨骼乃至脑机接口,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成为现实。而这也恰恰顺应了科技发展的主旨,即“想办法把我们从生物性本身对我们行动和理解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在科技浪潮的推波助澜之下,人类纪已呈现出不可避免的自反性,后人类纪元正在悄然降临。人类中心主义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一个必须重新界定人类主体性的时刻。正如冯·诺依曼在一九四五年的一次对话中曾预言的那样:“科技的不断发展及其对人类生活所带来的改变……似乎把人类带到了一个可以被称为人类历史的奇点的阶段,这个阶段过后,人类的社会和生活模式就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在人类纪向后人类纪转型的巨大断裂当中,在福柯宣告“人之死”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奇点将至的此时此刻,探讨人的生物性其意义何在?

海德格尔曾将现代性的表征罗列为以下五者:科学,技术,艺术落入美学的管辖之中,一切人类活动都被设想为某种文化,诸神的隐退。而此五者的本质乃是人类将世界客体化为一种图画,亦即是,将原本作为整体的存在视为可把捉、可谋划、可操控的对象。以此为据,海德格尔进一步将现代性的根本事件总结为——“人们对作为图画的世界的征服。”世界成为图画,人成为主体,这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是现代性的必然效果,同时也是对世界和人的双重扁平化。
上述这一切正是人类对于世界的巨大支配力量的源泉,也正是人类纪之所以成立的形而上学根基。现代性令人类得以改造自然并就此发展出不可抗拒的文明,但也使得人类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世界制造巨大的问题。后人类主义者们忧心忡忡,纷纷提出了诸如“制造亲缘”“游牧主体”等口号,旨在重新考量人类这一概念。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主张从碳基生命向硅基生命的进发,还是倡导敞开人类概念、让人的主体性在创造性的生命力当中消融,我们总是需要不断地回到人的生命本身,更本质一点说,就是拨开“文化的人”“政治的人”所制造的迷雾,重新回到“物种的人”。这对于我们因应来自后人类纪的无数挑战有着刻不容缓的必要性。
自从进化论从神的手中夺回了人类的创生时刻,人的神性之光便告消散,作为物种的人迅速凸显出来。人被固定在他的生物性上,失去了其作为万物灵长的崇高与超越。尼采“上帝死了”的呼告中也回荡着进化论所引发的轰鸣,诸神隐退之后,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没有神的世界上生活,如何在永恒的不确定性立足,如何在“食色,性也”的生物性之外为自己生成意义,以及如何去爱(因为已经不存在一个爱着世人的神)。
生命与生命的差异没有我们想象的大。从蛋白质结构上看,人与黑猩猩的相似度是惊人的 98.7%,而人与水仙花的基因序列也有 30%的一致性,与香蕉的一致性更高达 60%。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一致性无非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断章取义,生命之间的贯通似乎还要超越于生物维度之上。
彝族的创世神话中有“雪子十二支”之说:天地混沌初开之时,始终无法造出人。后来,天空降下三场红雪,“以冰为骨,以雪为肉”诞育了十二个族群,其中有灵无血的有六种,分别是蒿草、白杨、水筋草、铁灯草、针叶草和藤蔓;有灵有血的也有六种,分别是蛙、蛇、鹰、熊、猴和人。可以想见,在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里,人只是万物的一支,与其他族群同样来自天地的化育。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与动物和植物是贯通一致的。这种程度的贯通恐怕还是老子讲得最为清楚明白,他以“道”统摄一切,认为“道”在万物之先,孕育万物,同时又内在于它们,所以,道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道是万事万物无以摆脱的共同本质。
那么,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人有植物性吗?”答案可以是肯定的。不但如此,哲学家们甚至以植物式的“根茎”作为观照世界的方法。
根茎,在德勒兹的意义上意味着无所谓主干也无所谓源头的植物根系,它不由单个的点构成,而是由不可胜数的线条缔结而成。在我的理解里,竹鞭(也就是竹的地下茎)或许正是德勒兹理想中的根茎形态。竹鞭有节,并且节多而密,节上长着须根和芽。其中,一些芽发育成为竹笋钻出地面,在适当的条件下迅速拔节,长成高入云霄的翠竹,另一些芽不长出地面,而是发育成新的地下茎。这些根茎在地底盘根错节,形成巨大繁复的网络,因此竹的生长往往成林成片、漫山遍野,竹笋也常常层出不穷、掘之不尽。

非但竹林,蚁群、狼群和鸟群也是根茎式的存在,“即使其绝大部分被消灭,仍然能够不断地重新构成自身”。正是由于根茎没有根源、据点和既定方向,因此可以无边无际地蔓延开去,成为一种不断生成的存在。传统树状思维强调植物的“根 -干 -枝 -叶”,强调一种主次分明的层级结构,而根茎强调的则是多元、差异以及对差异的重复。
乔治·R.R.马丁的《冰与火之歌》就是一个典型的根茎式文本。
这部小说采用多元叙事手法,以人物为切入点不断转换视角、更动视野,仿佛转动地球仪般向读者展示故事的面貌。然而任何一个人物的任何一段叙事都只反映某时某刻的事件片段,从根本上讲,故事的全貌只能在不断的拼贴中生成,而永远无法进行全景式把握。而当我们读罢掩卷,再回望这个文本,会发现无论怎样阅读仍有大量事件处于半明半晦的幽暗之中,人物如何成长、阴谋如何达成,作者所展示的都只是洋面上漂浮的冰山,而尚有 90%的体积在海平面之下。
当然,在后现代写作中,对上帝式全知全能视角的消解早已不算新鲜手法,《冰与火之歌》的根茎化还体现在其内容上。我们会发现,所有那些稳居中心的人物,在出场不久即跌落神坛,或跌落于权谋的算计,或跌落于命运的重创:国王被野猪撞死,王后与亲兄弟通奸,最具男主相的史塔克公爵刚刚踏入权力核心就被砍了头,令读者惶惑于故事该何以为继。我们会发现,正面的词语都逐渐涣散,逐渐偏离轨道:煊赫的变得污秽——泰温公爵被射杀于恶臭的马桶之上;英俊的落下残疾——王国第一骑士失去了右手;温驯的学会了权谋——淑女珊莎逐渐成为铁血女王;执着于爱的失去了所有爱的对象——瑟曦太后孤独地坐上了铁王座。我们会发现,所有打算向中心进发的人,终究失去了唯一的中心,只有强烈的个体欲求在命运罗网中盲目地奔突。处于边缘的人们不断涌动,制造不可胜数的新节点和新关联。边缘人纷纷以更为边缘的方式成长起来:私生子雪诺背对权力核心所走的每一步,似乎都将带着他造出新的权力峰峦;无法行走的布兰获得了全知视野,他的灵魂可以附着在任何生物之上,从而超越了肉身残疾的束缚;开局悲惨、毫无尊严的丹妮莉丝,从被兄长变卖给野蛮民族的一件货品,成长为 Buff(增益)叠满、豪华头衔长如相声贯口的绝世龙母。

如此一来,作者马丁对于这场权力游戏的叙述最终变成了一个权力批判的奇妙文本。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力量也许正潜伏在非等级化、非层级制的结构当中,正孕育于边缘性、侧生性、亚文化和非主流当中,并且也正生成于各种状态的流通当中。
根茎看重关联甚于中心,看重流通甚于稳定,在根茎中动物、植物、世界、书籍、自然物和人造物……彼此关联。这样看来,用根茎来描述和解析网络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是再贴切不过的。正如德勒兹所说“在根茎之中,任意两点之间皆可连接,而且必须连接”,今时今日,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作为单个点位的手机、电脑以及其他电子产品连接在一起。这些点位的单个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当且仅当它们被纳入网络,通过无数信息川流不息的涌动,点位的功能性才得以发挥,其存在才被注入意义。
在信息漫灌的时代,身负根茎性的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吸收方式。今时今日的信息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人类难以承受的地步。一个数据爆炸的奇观:人类从直立行走到二〇〇三年间所创造的知识量总计五艾字节;而在二〇二三年,全球网络数据流量仅一年就达到了一千二百八十四艾字节;根据估算,该数据在二〇二八年将达到三千三百五十艾字节。在信息匮乏的时代,占据信息的人往往身居高位,被认为是聪慧与高超的,甚至具有某种先知性;而在信息泛滥的今天,不是人占据信息,而是人被信息无情地占据。有所觉悟者只能通过断网、关闭朋友圈或是强制性的人机分离,才能勉强夺回属于自己的时间和视野。据说,当人长期处于不健康的身心状态时,体内的植物神经系统会将外部世界识别为有毒性的,继而减少或是完全避免食物摄入,而这就是神经性厌食症的由来。植物神经系统不受大脑意志支配,即便是在人入睡、昏迷乃至失去思维和意识的时候,仍然如同后台程序般默默运作。它这种全自动开启、及时止损的自我保护模式,在冗余信息如洪水般无节制漫灌的今天,倒不失为一剂良方。
在过度分享的时代,身负根茎性的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呈现方式。今时今日的分享,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世界图像的再现,因此这些分享并不具备更超越的视野,也不采取更整全的方法,更不蕴含人与存在因彼此敞开而产生的深层领悟。它们仅仅是人单方面地打量存在,并将存在作为客体来进行描述的结果,因此注定是碎片化的、肤浅的和割裂的。德勒兹借由“无器官的身体”试图向我们揭示超越身体主体性的可能,倡导将身体作为事件本身,或者说,身体就是事件本身。根茎不表征大地,根茎也不再现它所在的空间和世界,根茎只是不断地自我敞开,并与世界同生共在。人也该当如此,人不应再把自己作为再现世界图像的渠道,而是去发现一个充分的外部,而这个发现使得人能够更好地统一于异质性,从而获得自由,并得以进行自由的创造。小时候我读安徒生,《海的女儿》的结局令我十分不解——小人鱼跳入海中、化作泡沫,但这并不是灭亡,她感到自己获得了轻飘的形体,与无数跟她一样的缥缈生物一起向着天空的女儿走去。她将有三百年的时间,通过为天地万物造福,给自己创造一个不灭的灵魂。现在我知道,作为一个爱情故事,不被爱的人化作泡沫确实过于残酷,但如果把它看作一个哲学故事,那将开启一重全新的境界。这个结局更像是在说,以崇高的爱情和自我牺牲为命定的锁匙,小人鱼进入了某种全然的敞开之境,并由此超越了其既有的身体和器官,汇入了更高的阈限,她的生命进入了新的维度,并获得了更为自由、更具生成性的自我呈现。

在拒斥深度的时代,身负根茎性的人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与外界的连接方式。世界图像化时代的人类交往日趋肤浅、关联日趋脆弱,与自然隔阂,与他人疏远,也隔膜于自己的内心。各种规格的电子屏幕使得我们在“在场”与“不在场”之间切换自如,但也使得我们的“在场” 和“不在场”都既不彻底也不纯粹。根茎的本质就在于那个连词“和”,通过“和……和……和……”来制造点与点之间的强联系才是根茎性的关键。这样看来,《红楼梦》中的海上仙方“冷香丸”可以说大有意味。“珍重芳姿昼掩门”的宝钗是一个天生的疏离者,多年的礼教束缚和自我规训,使得她成为大观园中离本真状态最远的少女(与最具植物性的黛玉分属两极),事实上她也是最早搬离大观园的女子。冷香丸药方是将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白梅花蕊各十二两研末,并用同年雨水节令的雨、白露节令的露、霜降节令的霜、小雪节令的雪各十二钱加蜂蜜、白糖等调和,制成丸药埋于花树根下。发病时,用黄柏十二分煎汤送服一丸即可。所有这些花朵、时令、雨露霜雪和“十二”这一再复现的数字,在红学中显然各有解读,但我们不妨把它们统一视为以大自然为代表的天然本真。可见,这个药方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宝钗胎内带来的热毒,更是针对她与自然、他者和自身本性的疏离,药丸每年为她与本真状态进行一次链接,既是救渡,也是对她成为一个“真人”的诫勉。
与外界的连接如此重要,唐娜·哈拉维提出“制造亲缘”即试图打造人类与所有生物(乃至非生物)之间的强联系,从而为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建构一个避难所。对此,艺术家们提供了自己的思路。
二〇二四年三月到八月间,红砖美术馆在一场名为“共生”的展览中展出了阿根廷艺术家托马斯·萨拉切诺的作品。艺术家试图借由蜘蛛的生活向我们展示一种去中心化的网状生存样态。其中有一件作品布满了整个六千八百立方米的展厅,作品中的每一个点都与其他的点以某种方式巧妙地相连。观者穿梭其间,仿佛化身蜘蛛,又像是以蛛丝为弦奏响整个宇宙。这件作品曾被哲学家拉图尔评价为“塑造当今政治生态的有力尝试——通过扩展以前的自然力量来解决建构宜居社区这一人类政治问题”。生物并不应当仅仅被化约为原子,生物始终是混合、嵌套并且勾连于他者和世界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物获得了其生存的深度和广度。蜘蛛是建构关系的高手,蛛网即便在暴风骤雨中惨遭摧毁,蜘蛛也能凭借其对于世界的深刻体察和无与伦比的耐心予以从容的再造。萨拉切诺甚至倡议人类向蜘蛛致敬并学习,毕竟蜘蛛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三亿八千万年,而人类的存在迄今只有二十万年。

电影《草木人间》的开篇,是采茶女们在晨光熹微中走上茶山,齐声高喊:“茶—发芽!茶——发芽!”梦寐般的温润光线里,茶山间云气浮动,镜头拉远,一层层绿意不断堆叠起来,仿佛茶树真的听到了人的召唤,悄然拔节,就此开启新一年茶事。“喊山祭茶”起源于宋代,曾是一项隆重的官方活动。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诗云“夜间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呀。万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这项仪式的动人之处在于,它相信所有生命都从属于某个整全的自然体系,以此为前提,一种生命可以激发另一种生命。无独有偶,每年清明四川都江堰的“放水大典”上都有“打水头”仪式。从杩槎缺口处涌入的第一股岷江之水叫作“水头”,当它涌向川西平原的那一瞬间,堤岸上的堰工会以手中竹竿猛击水头,告诉它,此行千里务必驯顺听话,不毁桥梁,不毁良田,要为民造福。这上千年的仪典中保留着人确曾生活在一个未经祛魅的世界中的证据,那时候,人与世界彼此敞开、彼此共在,而在某些神圣的时刻,人可以跟水说话,而水也做出它的回答。
在仪式中,人可以与植物、与河流对话,因为仪式是对时空的重构,因此也就成为现代人回归自然序列的一个契机,也是人类身负其根茎性而自由生成的必要方法。正如韩炳哲所指出的,是仪式“使时间可以居住”。仪式的丧失是可怕的,因为那意味着生存在一个全然祛魅的世界上,居住在不断崩溃的时间里,与围绕着我们的一切全然割裂,而这势必导致灵魂的孤独、动荡与干渴,仿佛被大
力神托举而离开大地的巨人安泰,终将力竭而死。
罗马博尔盖塞美术馆有一尊大理石像《阿波罗与达芙妮》,出自雕塑大师贝尼尼之手。这件雕塑刻画了阿波罗对达芙妮的追逐,当他的手碰到她的那一刻,少女的手指猛然生出枝叶,足趾生出根须,她的双腿和躯干则迅速覆上了树皮。仙女达芙妮在惊慌失措的奔逃中化作了一株月桂树。

今时今日,在现代性的穷追不舍下已然筋疲力尽的人类,似乎也来到了如此惊慌失措的时刻。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20737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