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在爱荷华天空下
作者:蒲实
11-19·阅读时长12分钟

爱荷华的文学之家
1983年,香港作家、编辑家和出版家潘耀明参加了IWP项目。同期来的是内地作家茹志鹃带着她的女儿王安忆,还有一位是吴祖光。潘耀明当时管理《明报》出版社,与内地作家已有一些业务往来。爱荷华写作计划的成员都住在“五月花公寓”里,两个人共用一个厨房。当时项目给每个人一个月2000美元的补助。中文作家不太习惯这种集体生活,聂华苓给予了特别的照顾。她喜欢设宴请客或在自己家里下厨,请大家去聚会。
潘耀明告诉我,聂华苓喜欢在两个地方请客,一个在燕京酒楼,是中国人开的;还有一个西餐厅,叫电力公司(Electric Power),多是宴请外国作家。这两处的聚会,聂华苓都会叫上潘耀明。聂华苓自己也做菜,“她从台湾带去炭炉火锅,厨具器皿很齐全,作家们的聚会若在她家里,每个人都带几个自己做的菜去,这样的聚会每个月有两三次”。
聂华苓在生活上、金钱上和精神上给予了参与写作计划的作家们无微不至的关照。潘耀明回忆,写作计划结束后大家各自离开爱荷华,而他还要去纽约大学读出版和杂志专业的课程。他的英文不够好,就向聂华苓提出想在爱荷华大学进修英语。为了解决他的生活费问题,聂华苓邀请潘耀明去她的写作计划项目做助理研究员,每个月给他一点补贴,他便在爱荷华又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他的两个女儿也都送到爱荷华大学念书,也得到过她的照顾,这些都让潘耀明心怀感激。
爱荷华写作项目的基金来自美国,基金仅赞助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过去,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作家是不能得到赞助的,这两个地区的作家所有来回机票及在爱荷华食宿一应费用,都由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自己筹募。中美建交后,聂华苓可以邀请内地作家。从1979年开始,她在爱荷华写作计划中主持了一个“中国周末”文学活动。她第一次请来的大陆作家,一个是萧乾,一个是毕朔望。他们前往美国,途经香港时是潘耀明接待的。“大陆作家能够与台湾作家在爱荷华见面,当时非常轰动,《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都进行了报道。聂华苓开拓了两岸作家相聚的机会,她很不简单。”潘耀明说。
爱荷华项目将作家聚集在一起,每一个地方来的作家需要准备一个主题演讲,比如当时茹志鹃和王安忆主要讲的是大陆小说和她们的创作体会。其他主要是作家自己的交往,大家住在“五月花公寓”里,很方便约着一起出去聊一聊。华人作家的英语普遍比较生,聂华苓专程请了翻译系学生,每位作家配备一位,方便他们交往。1983年的时候,王安忆还没有名气,更有名的是台湾作家陈映真,他坐过九年多的牢。这些台湾和大陆作家之间彼此有了交流和印象。爱荷华项目结束后,茹志鹃邀请过柏杨夫妇到大陆,那是他们在1949年后首次踏足大陆;陈映真也与吴祖光、王安忆结成了好朋友。
爱荷华项目结束后,通过聂华苓的推荐,潘耀明去了纽约大学读出版和杂志专业,这对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很大帮助。到了纽约,他在《华侨日报》的副刊做了一段时间编辑,邀请了在爱荷华写作计划认识的一些作家,包括柏杨、夏志清等来写稿。金庸先生请他去做《明报月刊》总编后,王安忆、陈映真、吴祖光都成为《明报》作者队伍的一员,他在香港的出版社出过他们的书。这种文学上长存的友谊一直持续至今。
潘耀明说:“聂华苓有很开阔的文化情怀,她是超越地域、超越政治、超越了很多界限的。这种精神力量是她人格魅力和能量的来源。她能够容纳不同文化、政治背景的作家,只要在文学上有贡献,她都一视同仁地邀请她们。这是聂华苓能够做这么大,能够组织这么多人的原因。”
半个世纪以来,对于参加过爱荷华写作计划的作家来说,这个项目具有文学之家的意义,用潘耀明的话说,“回到那里就像回家”。2017年,他在爱荷华遇见了那一年项目的参与作家,毕飞宇、董启昌和痖弦,他们一起庆祝聂华苓IWP50周年,在爱荷华的天空下相聚。他回忆说,那里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气息,“那是独属于聂华苓的气息,来源于她广阔的胸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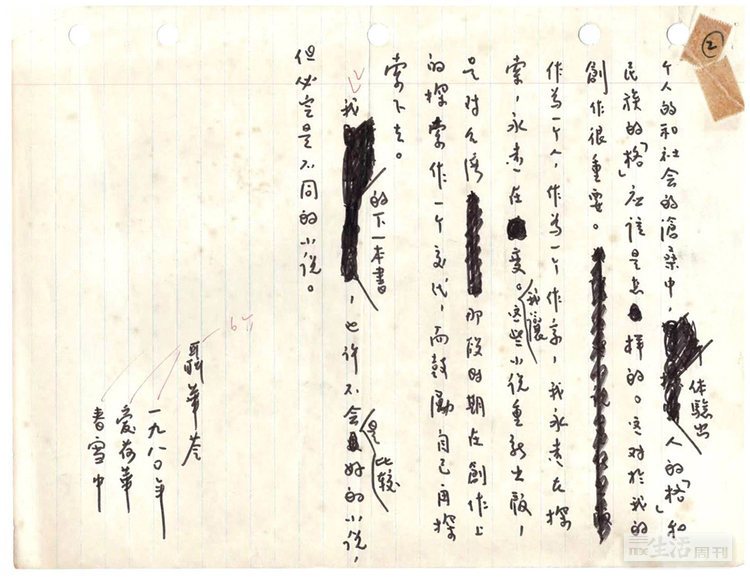
历史时空里的相遇
2018年,诗人、数学家蔡天新参加了爱荷华写作计划。他是受爱荷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叶扬波邀请前往的。叶扬波与聂华苓关系很好,也热爱文学。
他是8月份到达的爱荷华。写作计划的开班仪式在一处临湖的会议室。那天,蔡天新了解到,这座中部腹地小城爱荷华对于美国文学版图来说原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颁发了世界上第一个创意写作硕士学位,美国大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雷蒙德·卡佛都曾来求学,有40多位普利策文学奖得主和7位桂冠诗人曾就读于爱大或在此任教。
在叶扬波的陪同下,蔡天新在一家中餐厅见到了聂华苓,“她订了临河的席位,窗外有一个小瀑布”。那天参加午宴的除叶杨波和夫人钱放,还有聂华苓的妹妹聂华蓉、女儿王晓蓝。此时的聂华苓已94岁,“依然谈笑风生,只不过记忆力有所衰退”。
8月和9月,他再次拜访聂华苓。聂华苓的家在一座临湖的小山坡上,“一幢两层的老式木质红房子,前门有一片小巧的草坪,后门只有一个停车位。但下面七八米处有较大的空地可以停车,有扶手的木楼梯与之相连”。在一楼的书房里稍坐,蔡天新仔细打量了她的客厅,书桌上方两米多的莲花水墨画是画家黄永玉于1999年赠给聂华苓的,上面写着“要再为安格尔画一幅画/像古人挂剑在朋友的坟前树上”。另有一幅黄永玉1980年赠的水墨花鸟画,写有“有美人兮在水之湄”字样,挂在二楼酒柜上。长沙发上方靠门边的墙上挂着画家杨之光的两幅人物肖像,画中聂华苓笑意融融,安格尔温情安详。对面的玻璃镜框里,是茅盾先生1973年夏天写的一首词,他用钢笔竖写抄录给聂华苓和安格尔,时间是1979年。
10月,蔡天新与叶扬波再次去看望聂华苓。那天酒过三巡,蔡天新与聂华苓聊起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聂华苓喜欢与来客回忆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她向蔡天新讲起1937年抗战爆发后她母亲带着全家到湖北乡下三斗坪避难的经历,以及1944年她本已经被保送西南联大,但最后时刻选择入读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经济系,随后转入外文系的经历。
在爱荷华,蔡天新遇见了来自日本、印度尼西亚、乌克兰和印度的新锐作家,与他们畅谈在世界各地的旅行和中国古代诗人杜甫。同样参加过IWP项目的韩国作家许世旭把聂华苓小山丘上翼然临于爱荷华河的独立屋比喻为“四海苑”,说聂华苓的阳台上“常搬来一个地球”,欢聚了来自世界不同国籍的作家。
诗人西川2002年参加IWP项目,那是他第一次到美国。他没课的时候就会去别的地方旅行,去了很多地方。国际写作项目也很丰富,组织了各种活动和研讨会,这些研讨会不光是关于文学的,也关于政治和历史。“我记得有一次这个研讨会请了一个中东问题的专家来讲中东问题。在国内,中国作家很少关心国际政治问题,中国作家聚在一块儿不讨论国际政治问题,而是讨论你的小说写得好,他的诗写得好。爱荷华会让你越出文学边界来关心全世界和当下的历史环境。我可以看到文学以外的东西,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爱荷华大学的校园里,西川见到了去那儿朗诵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他当时已经得了诺贝尔奖,“沃尔科特在那儿做朗诵我们都去听,这就直接地跟国际文学界开始有了真正地接触。IWP内部的人是大家一起待几个月,这个是比较长时间的接触;听讲座则是短暂的接触,但你也看到国际文学界是怎么一个情况”。
与所有来爱荷华的作家一样,西川也常去聂华苓家吃饭,听她聊往事。她的这个房子曾经是世界各地的作家聚会的场所,他们之中很多人后来非常有名,比如之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慕克、莫言和韩江。后来西川再有别的机会去美国,每到爱荷华,他一扔下行李,直接就顺着记忆找去了聂华苓家,“那个房子有聂老师在,就像我自己的家似的,非常放松,我知道在那儿有一个像亲人一样的老太太”。
爱荷华大学有一个书店叫“草原之光”,西川经常跟孟京辉一起去听诗人朗诵。“这些诗人来自天南海北,你知道有的诗人挺好,有的诗人没那么好,慢慢你对于美国诗歌界和国际诗歌界开始有了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远距离观察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哪儿都厉害;等到近距离观察,接触的人多了以后,你开始能够区分谁真正的厉害,谁没那么厉害,一些关于外国文学的迷信也给破除了,与此同时,你对于真正重要的东西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自1991年安格尔突然去世以后,聂华苓一直一个人独住。“有时在附近小镇生活的妹妹会开车来陪她,但妹妹也已80多岁;还有一位小时工,每周来几次帮做家务活儿。她的女儿王晓蓝在纽约,偶尔也会飞来爱荷华探望母亲”,蔡天新回忆。50多年前,聂华苓与安格尔联手建造了连接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一座桥梁,而当2018年蔡天新来到这里时,中美正发生贸易摩擦。时移世易,已是不同时空,这种历史感在聂华苓的客厅里会在某个时刻向到访的人们扑面而来。

同一片天空下
爱荷华写作计划的开创者是聂华苓,支持者则是她的美国丈夫保罗·安格尔。两人的协作天衣无缝。
保罗本来是爱荷华写作坊的负责人,这个写作坊是美国最高水平的写作坊,开始于1942年。保罗从牛津大学回来以后接手了这个工作坊,由他发展起来,到1964年已为之工作了22年。保罗在台湾遇到聂华苓,并与她一起来到爱荷华时,他已邀请了一些外国作家来参加写作坊。实际上,聂华苓当年也是作为外国作家被邀请到“写作坊”的,与她一同受邀的还有菲律宾、阿富汗和韩国的作家。当时聂华苓曾向保罗提出建议:为什么不干脆办一个外国作家写作计划?保罗的第一时间回应是:“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但他很快着手去找拨款。1967年,第一批来的是台湾的痖弦,待了两年,之后是郑愁予;香港的戴天也来了,待了一年。就这样,IWP诞生了。
潘耀明回忆,聂华苓和她的先生在生活上都很简单。有一年她回武汉探亲时,曾请潘耀明去她家照顾保罗·安格尔,与他相处了两个月。他们的早餐是用老派器皿煮的黑咖啡,他通常吃完烤过的隔夜面包就去写信。保罗·安格尔是美国诗人的旗帜,在文学圈很有影响力,每天要给各种作家写很多信。聂华苓在家时烤好一只大火鸡,每顿饭给安格尔切一块火鸡肉,再配点沙拉,就是一顿。保罗也自己劈柴和清理游泳池,70岁还爬到屋顶自己修缮房子。“他喜欢穿着工作服做这些事情,经常说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的手非常粗糙,是长年劳动留下的,曾经有一位诗人写过一首关于保罗手掌的诗”,“他过着这样简朴的生活,但他做的事情是很伟大的”。潘耀明说。
保罗·安格尔去世后,聂华苓一直让他的房间和客厅保持着他去世那天的样子。那一天的《纽约时报》仍然放在那里,拖鞋、衣服像在等离开的他回来。1977年的一天,也是在这里,保罗早起阅读《纽约时报》时告诉了聂华苓中美已建交的消息,他们当即决定邀请中国大陆的作家来参加写作计划。保留这个房间的原样,是聂华苓感受保罗与她同在的方式。“保罗·安格尔留下了一份遗产,这份遗产就是他与美国文学界的关系。他曾经是美国中部很有影响力的诗人,能够把美国的文学资源吸引到爱荷华来。这个项目与美国的各种基金会有联系,不同作家去爱荷华接受的是不同基金会的资助,是项目办公室为作家申请到的钱。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也是在美国的基金会机制中运作的。”西川说。
IWP项目曾有过差点被取消的波折。聂华苓于1988年退休后,从1988年到2001年,她不再过问IWP的事,IWP也被边缘化,2001年管IWP的文理学院院长拟将项目取消。其时聂华苓正在北京访问,时任副校长恰好也在北京。聂华苓找到曾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他于1980年到过IWP。她请王蒙以中国作家协会的名义为副校长举办一个欢迎宴会,还让王蒙邀请参加过IWP的其他作家一道,以壮声势。聂华苓告诉潘耀明,王蒙当时是作协的副主席,他答应了,主持了欢迎宴会,说的话很有力量。那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已大大提升。副校长在宴会上听到中国作家对IWP的称赞和嘉许,返回爱荷华大学后,重新找聂华苓当IWP委员会的委员。从此以后,聂华苓便有了发言权,IWP又恢复了对中国作家的邀请,请了苏童、余华和莫言。
聂华苓不仅是文学的组织者,也是一位性情中人,她的内核有着传统的侠义精神。余华曾回忆,聂华苓每次请客吃饭都要数百美元,但却舍不得花四五百美元为自己换一台好一些的电脑。有人说聂华苓在大陆亲右派,在台湾亲左派。对此,聂华苓说,一旦到文学这里,政治就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人与人的关系。1983年的那一期项目还有两位作家分别来自东德和西德,两个政权之间尚未对彼此开放,爱荷华成为他们相遇的文学“第三地带”。两人在爱荷华虽然激烈争论,却在机场告别时相拥流泪。当柏林墙还在现实世界矗立时,在爱荷华的天空下,这堵墙已被事先拆除。
聂华苓曾这样讲述她的过往与身份:“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在外省之中,我又是个外人,总是外外外,一层层的外。”从台湾到美国后,聂华苓身份和认同的转换和裂变,促使她写出《桑青与桃红》这样的小说。她体会到20世纪的人处境的分裂、心灵的分裂和人格的分裂,她感到自己对台湾和大陆都有感情,却流放了一辈子。她说,她在台湾是大陆人,在美国是中国人,在中国是华裔美国人,有时不禁自问:“我究竟在哪里呀?”
在她一生并不顺遂的经验中,中国人的命运好像就是“逃”和“困”,但聂华苓并未因这种悲剧性的命运而变得狭隘,相反,她将这种命运放到了20世纪人类命运的更大图景中,看到了这种命运与世界其他各地人的共同之处,从而得出“它也正是20世纪人的普遍处境”的结论。这是她与国际文坛接触后得出的感受,也成为她创作的出发点。
台湾的白色恐怖对聂华苓影响深远,那种恐惧感一直回荡在她此后的生命中,也促使她离开台湾前往美国。然而,这种恐惧却推动她开启了两岸文学乃至世界各地作家的交流。正是这样一个“外人”,穷毕生精力,在爱荷华小城为世界各地的作家创造了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家”的地方,给予了许多作家归家的温暖。
西川最后一次见到聂华苓是2013年,她那时已经快90岁,长期记忆都在,但是短期记忆已经丧失了。她在记忆力特别健康的时候记住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对于十几二十年前的老朋友,她还能叫出名字来;但对刚刚认识的新一代小说家,她可能上午刚认识,下午便忘了名字。
2024年6月21日,潘耀明的次女潘宇翔专程从西雅图前往爱荷华探望聂华苓。她仍能清晰地回忆起许多爱荷华的旧事。潘宇翔回忆道:“……下午开车到爱城。到了五月花公寓,记得是旁边一条小路开上山。找到那红色的屋。按门钟,一个黑人女子走下来。我对她说来探Mrs. Engle,但她对我说聂阿姨在午睡,叫我晚上再来。我告知我开了两小时车才到,没法等到晚上。她回去看说聂阿姨已醒。我把父亲和我的名字写在纸上,请她给聂阿姨。这样我进屋了。聂阿姨说她记得父亲,她说有些朋友永远记得……”四个月后,聂华苓去了另一个世界。在爱荷华的天空下,她与保罗·安格尔同在。
文章作者


蒲实
发表文章153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1972人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