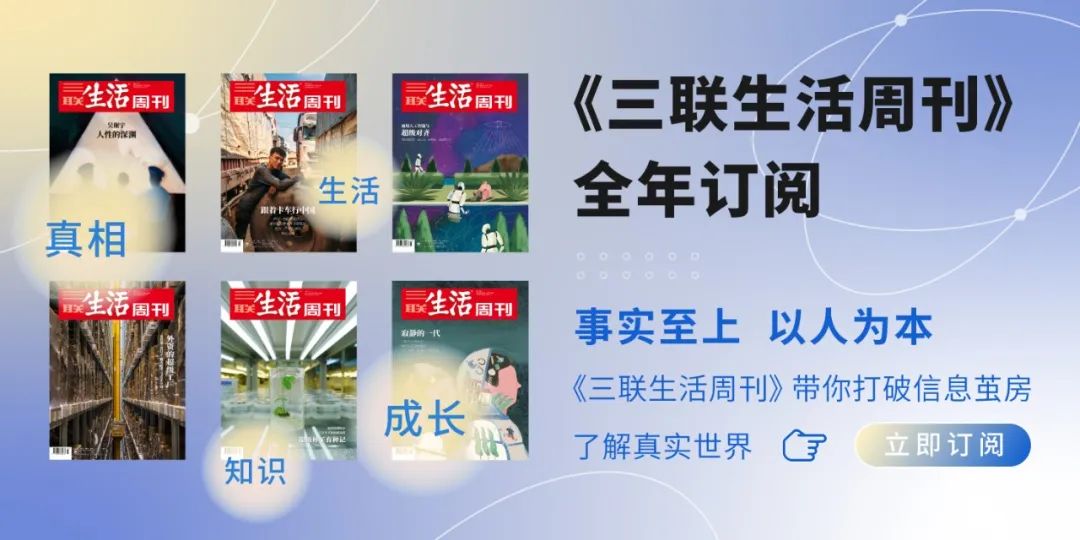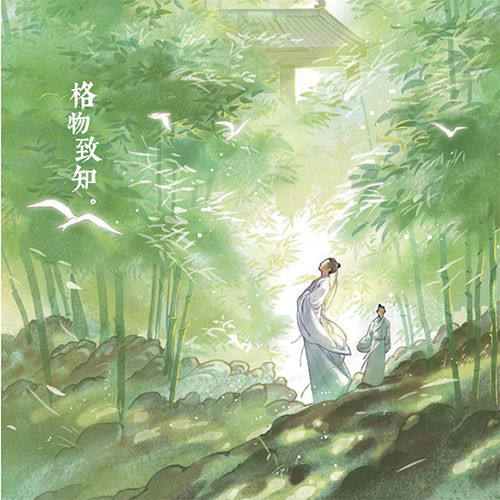越来越多为注意力焦虑的人,都在争相“认领”这个病?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7-25·阅读时长23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ADHD,全称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主要症状是注意力无法持久集中、过度活跃和情绪易冲动。ADHD无法通过生物标记物(如结构和功能核磁)被准确识别,其诊断长期依靠患者和父母的叙述,以及医生的主观判断。
正因为无明确生物指征变化,越来越多人开始“认领”ADHD,小学老师督促家长去医院确诊,成年人则“赛博自诊”。但ADHD的发病率真的上升了吗?一方面,更精细化的养育,大量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确造成了注意力下降,但另一方面,为什么那些原本被视为活泼、好奇的特性,也在被判断为多动、注意力不集中。
诊断ADHD的重要指标是,“是否影响正常学习生活”,而何为“正常”,这个标准本身就是在变动并值得审视的。
记者|王怡然
实习记者|曹泓
编辑|徐菁菁
ADHD,全称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主要症状是注意力无法持久集中、过度活跃和情绪易冲动。ADHD无法通过生物标记物(如结构和功能核磁)被准确识别,其诊断长期依靠患者和父母的叙述,以及医生的主观判断。
正因为无明确生物指征变化,越来越多人开始“认领”ADHD,小学老师督促家长去医院确诊,成年人则“赛博自诊”。但ADHD的发病率真的上升了吗?一方面,更精细化的养育,大量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确造成了注意力下降,但另一方面,为什么那些原本被视为活泼、好奇的特性,也在被判断为多动、注意力不集中。
诊断ADHD的重要指标是,“是否影响正常学习生活”,而何为“正常”,这个标准本身就是在变动并值得审视的。
记者|王怡然
实习记者|曹泓
实习记者|曹泓
编辑|徐菁菁
我的孩子正常吗
2023年,杨颖带着7岁的女儿走进上海一家医院精神科。她需要来确认一件事——女儿是否患有ADHD。
如果不是老师的建议,她完全没注意到女儿的问题。幼儿园时,杨颖发现孩子不愿意长时间写字,有些拖拉,但读书速度很快,画画时也很集中,她没想太多。没想到,一年级入学不久,杨颖开始时常收到老师的“投诉”:孩子做作业比班里同学都慢,是班上最邋遢的小孩。最频繁时,老师一周投诉了3次。
杨颖开始审视女儿的日常:别的孩子通常晚上八九点就能写完作业,但女儿一学期里,至少有十次会磨蹭到晚上十一点以后。写作业时,孩子总是溜号,或者写着写着就唱起歌;在生活上也是,花盆被打碎,要哭上四十分钟。杨颖也开始疑惑,这些从前没当回事的“坏毛病”,是不是意味着孩子“有问题”。

电影《小晓》剧照
在老师的要求下,杨颖带孩子去医院检测了ADHD。
ADHD全称为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是一种以注意力无法持久集中、过度活跃和情绪易冲动为主症的神经发育障碍,常在儿童时期发病,患儿常伴有学习困难、品行障碍、适应不良、睡眠障碍等问题。研究证实,ADHD人群大脑中特定的化学物质发生改变,且特定脑区(通常认为前额叶区)活动下降、发育不成熟,体积萎缩。
医院问卷的测试结果显示,杨颖女儿错了22题,而及格线是15题——不过,医生说,孩子并没有达到ADHD的程度,只是注意力极差,建议回家做些看沙漏、打乒乓球、练琴等注意力训练。
被要求带孩子求诊ADHD的不止杨颖,女儿班上还有其他几个表现“不好”的孩子的家长也收到了老师的通知。同样的事情也不只发生在杨颖女儿的班上。
深圳市康宁医院儿少精神科医生王中磊告诉我,来医院就诊的绝大多数孩子都是被学校老师发现“异常”后推荐家长带来的。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薛贵说,也常有家长把电话打到他这,询问孩子注意力不集中该怎么办。
如今,患有ADHD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吗?目前并没有基于大样本的流行病学研究证实这一点。求诊ADHD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一场“注意力危机”正在两端发生。
一方面,生活中确实存在许多引发人注意力下降的东西。
薛贵解释,长期处于分心、多任务的状态——比如大量使用手机、刷短视频——多巴胺系统和执行功能的大脑前额叶系统都会发生生理变化,长时间就会造成大脑器质性病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会变得越来越焦虑,焦虑会导致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形成恶性循环。
带女儿在医院就诊时,杨颖也反思了自己的教养模式,比如买了很多书和益智玩具堆在家里,填满孩子生活的空隙。医生告诉她,密集的安排需要孩子不停转移-集中注意力,可能超出孩子能够承受的限度,也是影响注意力发育的一重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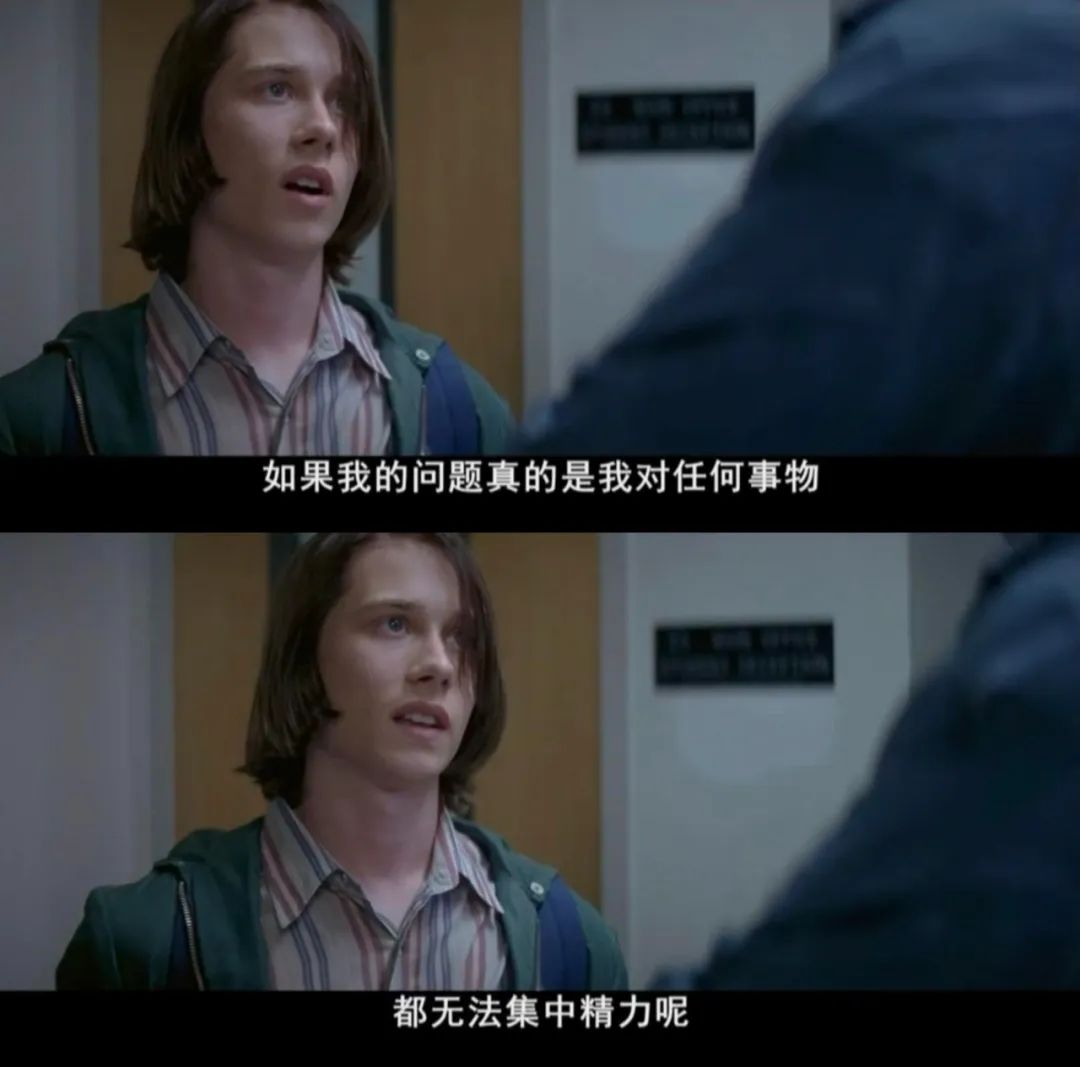
《吮手指的人》剧照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奎指出,现代精细化育儿方式下,家长对孩子的陪伴时间大大增加,但陪伴往往变成监督、变成忍不住对孩子自主活动的过度干预或打断,比如孩子独自玩耍会时不时出声逗弄,拿其他玩具吸引孩子注意力,在孩子专心看书或画画时,一会送水果,一会问作业、一会关心冷不冷或热不热等。特别是一些家长喜欢全程陪孩子做作业,看到孩子一有错误、甚至字写得觉得不好看,也要说上几句。这些行为都使得孩子注意力被碎片化,无法专注当下任务。越小的孩子,神经可塑性越强,影响就越明显。
“注意力危机”的另一端,是外部环境对注意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薛贵说,大多孩子都是在小学一二年级时确诊的ADHD。因为这时从幼儿园转移到规章制度更严格的教育体系下,一些大脑发育稍慢的孩子的差异就会凸显出来,出现无法完成作业、上课乱动的情况。如果环境宽松,这些表现不会和疾病挂钩,多动也可以被视作活泼,注意力不集中可以被视作对世界充满好奇。
作为精神类疾病,ADHD无法通过生物标记物(如结构和功能核磁)被准确识别。尽管依据DSM-5(《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对ADHD进行诊断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但在薛贵看来,评判的标准依旧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ADHD的诊断需要使用到量表和评分。以广泛用于评估儿童(ADHD)的“Connor’s量表”为例,它有三个版本,分别提供给家长、教师和临床医生,让他们对儿童行为进行观察和打分。
在家长使用的量表中,家长需要回答各种问题,在“没有”、“很轻”、“较重”、“严重”中做出选择,然后产生相应的分数。这些问题包括孩子“是否有学习困难”,是否“害羞”,是否“比同龄孩子更容易闯祸”等等。显然,如果教师和家长对孩子的主观要求更高,也就更容易选择孩子存在“异常”,更倾向于让孩子接受医学诊断。
身不由己
女儿就诊前后,杨颖也会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在农村疯跑疯玩,回家没什么作业,也没有老师在意她是否听课。而如今,女儿刚上一年级,在学校上课的时间从早上八点持续到晚上五点半;课间不能去操场玩,也不能追逐打闹;回家做作业到九、十点;周末通常有三节课外班,还要加入博物馆参观、研学等活动,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

《地球上的星星》剧照
事实上,持续的压力与过重作业负担本就会对注意力产生损害。刘正奎介绍,处于持续高压状态,肾上腺激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会过度释放,会引起海马体萎缩和杏仁核过度活跃,影响记忆和增加焦虑情绪,同时不利于前额叶的发展。要求孩子过度专注作业,不会锻炼注意力,反而会造成损耗,就像在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上开车,连续开二三十公里就会疲劳,因为在不断地刺激单一的脑区。
作为医生,对于下诊断,王中磊非常谨慎。诊断“ADHD”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看症状“是否直接负性地影响了社会和学业/职业活动”。王中磊认为:“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我给你下这个诊断,扣上这个‘帽子’,有什么必要呢”?即使下了诊断,在王中磊看来,家长如何看待孩子、调整自己的期待、调整养育模式来帮助孩子成长,才是更重要的事。
但很多时候,一个孩子被确认为注意力不够好,不一定就能得到恰当的帮助。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李晓茹现在正负责一个名叫“小松鼠”的项目,为有注意力缺陷的孩子家长提供支持,指导家长如何面对孩子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困难与问题。
作为心理学家,在李晓茹看来,“从一个小朋友毕生发展来看,神经发育的速度与他人不一致、不同步太可以理解了,很可能这是他的节奏,既不能过早下结论,认定为发育障碍,也需要有科学态度”。从神经发育来看,“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来自孩子的特质、成长节奏和他所生存的环境之间的要求不能匹配上。”
“坐着要小手背起来,写字要把双手放在桌上,右手拿笔,都是这种姿势,但凡出现一个歪着头或者斜着身子的,让拿笔没拿笔,用一只手扶着桌子,在这种环境下都是‘异类’。”李晓茹说,随之而来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作为老师和家长,大多会责怪孩子不守纪律、不认真、不努力,长期的负面评价与批评打压,容易导致抑郁、焦虑等各种问题。”
对于家长来说,很多时候身不由己。为了给孩子“减负”,杨颖停掉了孩子周末大部分课外班和活动,扔了家里许多东西,但学校的课业她无法干预。无论是老师的反馈,还是和其他孩子的对比都在告诉她,女儿就是更“差”的那个。现在,看到女儿写作业时溜号,她会控制不住地生气。
姜雨萌是另一位受到同样困扰的家长,她7岁的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没有打架、违纪等严重事件发生,作业按时做,成绩也不差,怎么看都是一个普通的小孩,但老师每隔一两天都来“投诉”——让孩子翻书的时候没有翻,孩子上课又乱动了——说来说去就是孩子注意力差又好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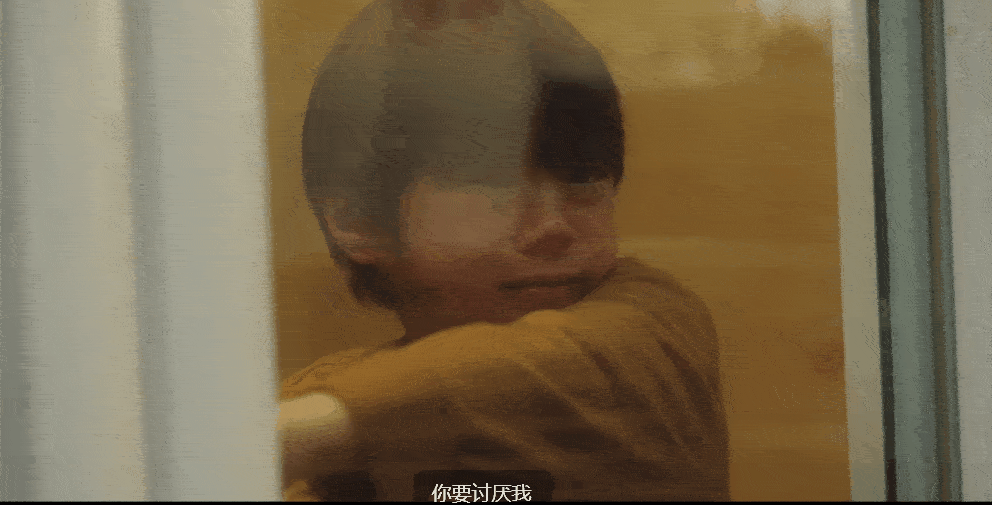
《我们与恶的距离2》剧照
姜雨萌想,对于一个7岁的小男孩来说,这些行为真的不正常吗?但老师的一句话说服了她:“现在一年级不培养好的学习习惯,到了三年级作业多时就跟不上了”。3个月前,她为孩子报了一个注意力培训机构,每月一万多元,上个月,又派孩子姥姥去学校陪读。这对孩子的学习成长究竟能起多大帮助,她也说不清,但至少现在,她不会再被老师三天两头的消息折磨。
“赛博确诊”
不只是孩子,在成年人的世界里,“ADHD”也开始变得“流行”起来。
我的朋友李佳是一名记者,“赛博确诊”为ADHD有一段时间了。最初,她在网上看了科普,觉得自己条条都中:写稿的时候不专心,不能一气呵成地写完,总是写着写着就去玩手机;不能完成2个小时以上的采访,对方说着说着她就走神。作为同行,我提出疑问:这些“症状”,任何人都会有吧。但李佳回忆自己小时候就被评价“小聪明”,“坐不住板凳”,对“自诊”的结果比较自信:“我感觉我就是,80%的可能吧。”
覃艳华是浙大邵逸夫医院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门诊的医生。她2014年开始从业,但直到2021年院里准备开展成人ADHD门诊时,她才第一次听说这个疾病,培训“上岗”。但这两年,像李佳一样“自诊”的成年人越来越多了,覃艳华深有体会。他们医院是2022年开放门诊的,每周的周三下午,固定放15个号源。最初,一天只有两三个人来挂号,从去年开始,门诊一下爆火,基本只能挂到三周后的号,大多人走进诊室的理由是:我在网上用自测量表测出我有ADHD,想来确诊一下。
面对激增的患者量,覃艳华心情有些复杂。一方面,过往医生和患者都没有成人ADHD概念,不少真正的ADHD被误诊为抑郁、焦虑等其他精神疾病,怎么治都“治不好”,认知的普及是件好事儿。但另一方面,网络提供的信息太泛化,给人“误导”,许多来看病的人,都不是ADHD。她特意做过统计,来访者中最终被确诊的,只有3/10。
按说,被医生排除了患有疾病,本来是件好事,但在覃艳华的诊室里,很多人的反应是情绪激动,问她:“量表上这些症状我都符合,你凭什么说我不是?”极端的人甚至要去投诉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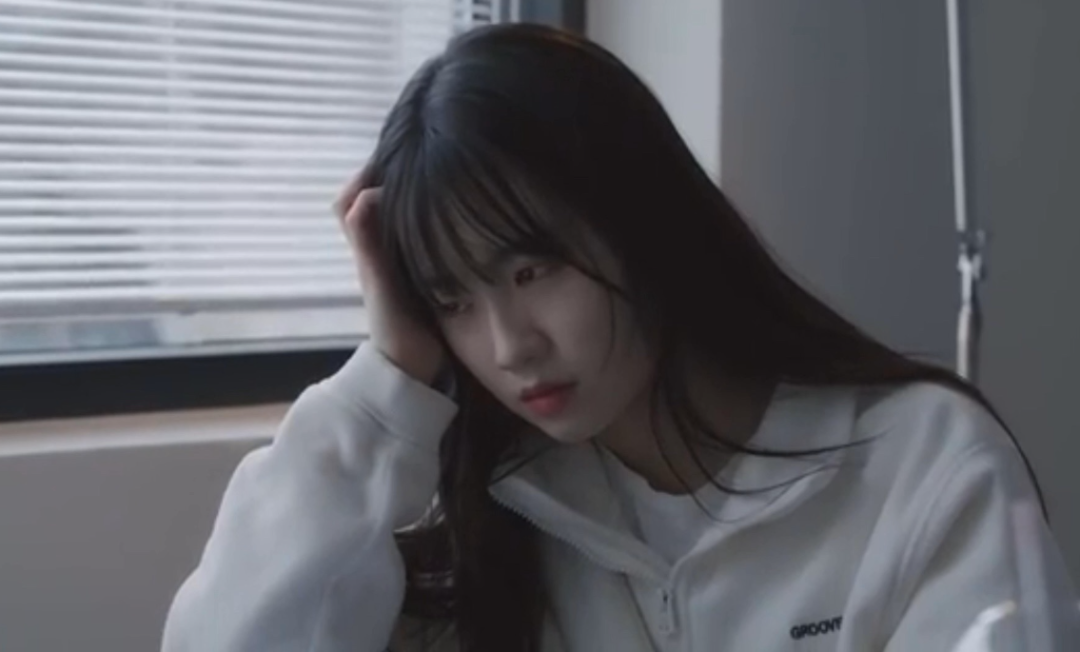
《我是ADHD吗?》剧照
覃艳华发现,很多人是在考公考研期间“自诊”的,她也搞不清,他们是学习压力大,要求高导致的认知错位,还是只想开出“专注达”(盐酸哌甲酯缓释片,ADHD适用药物)。由于抑郁、焦虑也会引发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覃艳华也会推荐一些来访者,再去其他精神科门诊看下。
医生的解释并不能平息互联网上“人均ADHD”的现象。翻阅社交平台,不少人在“科普帖”下面回复“每条都中”“原来我是ADHD”。
李佳的自我诊断来自对比,她举例说,有个同行经常在朋友圈发文,称与受访者一口气聊了3个小时,采访内容有一本书的体量,一天写完一万字……等等。这些数字量化的成果持续刺激李佳,让她产生挫败,“为什么别人都可以,但我不行”。这种情况下,想想自己可能是ADHD,李佳感觉舒服多了。
在李晓茹看来,李佳这样的自诊者是在用ADHD来应对“理想自我”——他者塑造了理想的具体形态,而理想和现实之间差距越大,对自我的不满足会导致自责和批评越来越多。
在复旦教书的李晓茹说,曾有不少学生课后主动找到她,认为自己应该是ADHD,要不要去医院确诊。李晓茹会问他们:这个诊断对你有什么意义?在她看来,如果通过确诊得到的解释,能让人更加理解和接纳自己,那确诊是件好事。但如果确诊后,只会给自己贴上“有病”的负面标签,增加精神负担,那诊断毫无必要。而比医学诊断更重要的其实是,面对问题,能不能找到对应的办法悦纳自己,找到适合自己大脑的生活方式。
小林是另一个被ADHD困扰的同行,但困扰的方式有所不同。她说自己从小就背不下来古诗词,三角函数只能记住一个公式,其他全考上考场现推,作业只有在“再不交就会产生无法挽回的后果”的恐惧中才能开始动笔。她一直坚信自己就是一名ADHD患者。去年,她心血来潮,去北京一家权威的精神科就诊。在做了量表和一些注意力测试后,医生几乎没问她什么问题,就告诉她,所有的数据都显示她有ADHD,注意力还不如13岁小孩,问她要不要吃药。她反而立即产生了怀疑,“你就这么草率地判断?我能相信你的结论吗?”小林没有开药,直接走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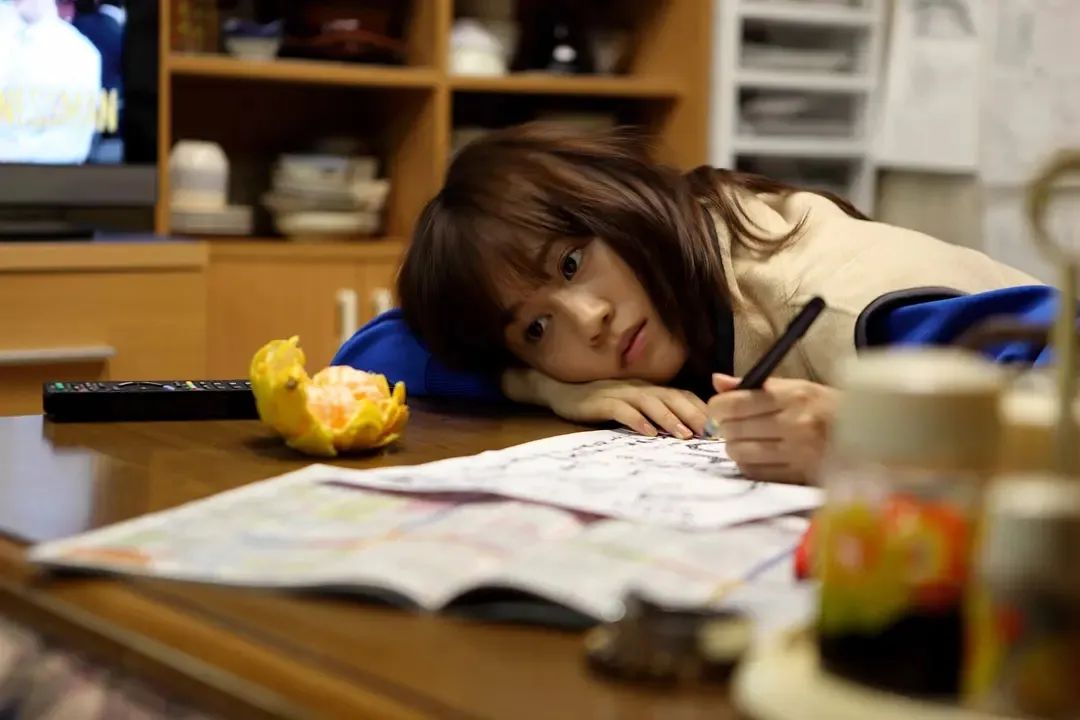
《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
一个月后,因为一次工作不顺,小林还是回去开了药。服用专注达后,她确实体会到了“正常人的世界”。因为抗拒工作大哭2小时的事,再也没发生过,做事也更“高效”了。“这是我”?小林自己都不敢相信。但药物之外,小林生活的另一个很大的变量是,她离职了,变成了自由职业者,工作合作伙伴对她远比原来的领导更包容。现在小林会不由得想:“我怀疑自己不是(ADHD),因为我其他事,做得都还行”。
“身体疾病和心理疾病在评价方式上的很大不同,在于我们到底如何去理解一个人因为一些症状而产生的功能上的损害,如何评估他的痛苦来源,痛苦的强度。有些就是痛苦强,必须去治疗和干预。有些他哪怕有同样的症状,但是他的生活还不错,就不用去治。疾病与健康于医学而言有明确的边界,但异常与正常对个体而言只有一个相对的评价方式,这之间的弹性空间是极大的。”李晓茹说道。

排版:球球 / 审核:雅婷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4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36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