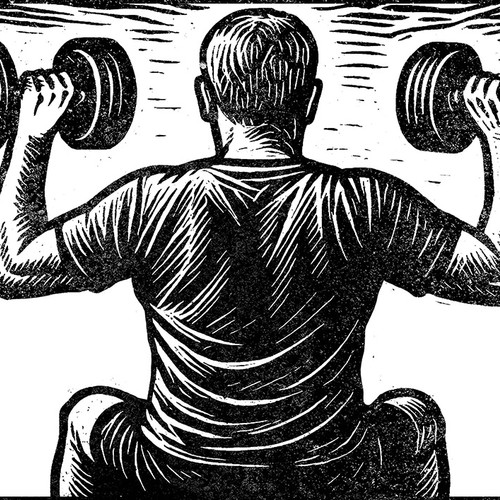教师节or教师劫
作者:大连左岸
2019-09-16·阅读时长2分钟
有些阴暗,需要晾晒——
教师节or教师劫
甫一开学,朋友便向刚升入高中的孩子班主任送去2000元钱——教师节在即,与老师感情破冰。在朋友看来,即使不奢望能被格外关照,也求个不被另眼相待的心理安慰。
钱是以现金形式,当面交接的。这在网络支付无处不在的当下,看似颇不合时宜。实则是别有隐情——电子支付往来留痕,容易授人以柄。现金,却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高枕无忧。
朋友对这套操作轻车熟路:小学六年,每学期给班主任500元;初中三年,每学期给班主任1000元。课任老师则弹性较大,多寡不一,送否不定。早期是现金、转账或购物卡,后期则全部转为现金。
送的时节,主要集中在教师节和春节,实际上,以前者居多。专属节日里,如果不做些什么,家长心里是惴惴不安的;至少,与老师见面时,仅仅以一句“祝老师节日快乐”口惠实不至的方式,或多或少,会有些“尬”。
接受礼金的老师,最多会有些礼节性的推辞。剩下的,竟如握手、打招呼一样,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没有任何违和感。亲历、耳闻和目睹送礼的种种,其中的坚辞不受者凤毛麟角。至于,这些钱能否起作用,又能起多大作用,全凭收钱者的“职业操守”了。
主流语言体系中,这种现象被定义为极为个别的害群之马。从自己十多年与孩子一众老师交往的现实体感,以及周遭家长的境遇,甚至更远处的各种吐槽来看,并不是每一个老师都“雁过拔毛”,但,被社会和家长“宠坏”的害群之马却不是那么“个别”。
此类状况的出现,积弊于家长规避风险的羊群心理推波助澜:即便心中一万个不愿意,都乖乖照送不误。因为,鲜有人愿意尝试,反正,也是为了孩子,也就不差钱儿了。受“老师可能记不住谁送了,但会记住谁没送”的自我恫吓和自我教育,随大流的心理和姿态便裹挟了更多的人。
向老师送钱,在家长中间是心知肚明,却难以公开言说之隐。只能和私交较好者之间相互谋划出参考价,而后各自执行之。大庭广众之下讨论此类话题,似乎是还是个禁忌。
排除正常的礼尚往来,送钱物现象,一直都存在。不管外部形势的宽与严,差别仅仅在于隐秘程度。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孩子未来的期许,送钱家长的范围和钱的“厚度”在扩展。
班级学习成绩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送钱的主力就是中间部分家长,特别是成绩中上水平水平的学生家长。一重点高中老师曾对儿子位居校百名榜前列的家长说,教到这样的学生是老师的荣幸,恨不得能给家长钱……送钱的激烈程度,按乡镇、县城、城市曾阶和地域经济水平递增。北京的朋友曾说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近几年教师节,送礼给老师统统吃了闭门羹;在此之前,类似节日临近,老师早早就开始指点迷津了。
人不能仅有事业,还要有副业。教师以自身资历和学识赚钱,是无可厚非的事。比如,本地就有1000元/小时、甚至更贵的高三一对一补习班。施受自愿,各得其所,只要不影响教师的正常教育教学,不失为教育资源市场化的有效途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没有付出,仅仅因为处于焦点的位置,便坐地起市,像收取保护费一样,安之若素笑纳家长的血汗钱,在三观正在形成的学生面前侃侃而谈理想、情怀的时候,是否扪心自问:我的功德呢?我的道德呢?我的品德呢?
不管世界商业味道如何浓郁,还是希望教师节能清朗、纯粹一些,成为涤荡污浊、清明社会一泓碧泉。让公众发自灵魂深处的敬重和景仰,铸就师者人格与尊严的金身!
文章作者

大连左岸
发表文章5篇 获得4个推荐 粉丝1人
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鹭齐飞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