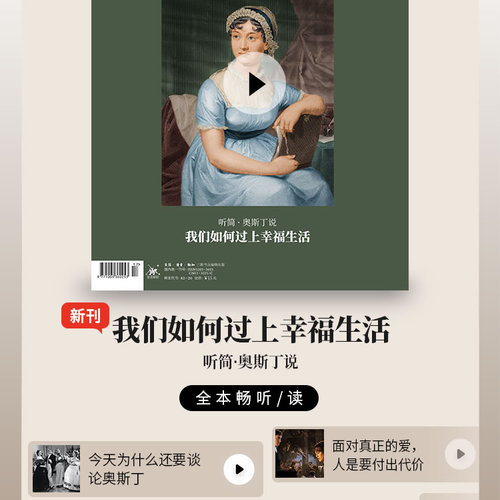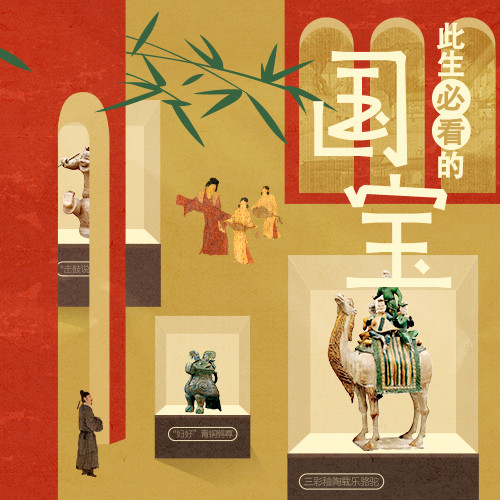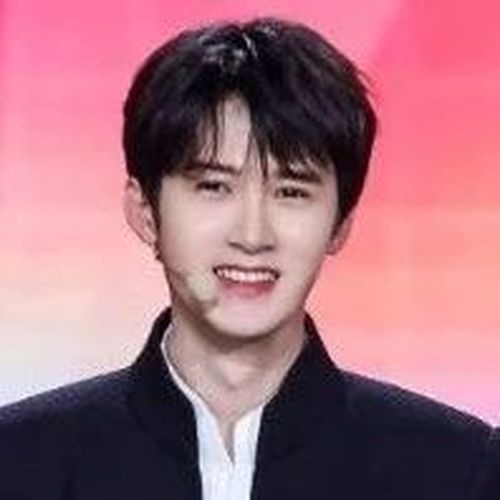帕慕克和他“脑袋里的怪东西”
作者:孙若茜
2018-02-05·阅读时长6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3236个字,产生2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和他的著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
虽然在人们的印象中,华兹华斯是热爱自然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但帕慕克恰恰把他的话用在了城市:“身处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可能感到孤独,但是让城市成为城市的东西,也恰恰是这种能够在人群中隐藏自己头脑里的怪念头的可能。”显然,书名不仅寓意人物的想象,也指那座主人公不停行走其间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是的,帕慕克又在写伊斯坦布尔了。和《我的名字叫红》里面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不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把时间轴定在了这座城市的1968到2012年。作者也不再写和自己更贴近的中产阶级,而是去写一个街头小贩——麦夫鲁特·卡拉塔什,几乎从1970年开始,他就在伊斯坦布尔街上卖钵扎。通过他的眼睛,帕慕克在笔下展现了土耳其40年间的社会变迁,相比他过去比较个人化的视角,这一次作家对伊斯坦布尔的审视和记录应是更加全面、更加真实。
麦夫鲁特是典型的底层阶级,这也许会让你想起以往读过的狄更斯——那种书写小人物种种奇遇的故事。帕慕克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自己对狄更斯的喜爱,喜爱他的语言和幽默,但这种喜爱有限且克制,他不喜欢狄更斯的煽情故事,“有的时候,他让角色喋喋不休,非黑即白,显得滑稽”。因此,在这本书里,虽然帕慕克的确特意设置了一些狄更斯式的人物,但它并不是一个煽情故事。“创造一个表面化的或煽情的催泪角色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这儿这个小伙子和你我一样非常正常,还贫穷潦倒。我可能一直在悄悄地对自己说——别管他,你会发现他有意思。”有意思的平常人,这大概就是帕慕克花了6年时间试图在书中塑造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格,所想要麦夫鲁特成为的样子。
文章作者


孙若茜
发表文章103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708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