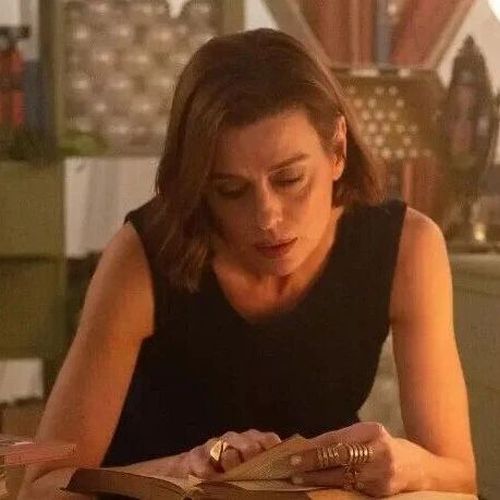“ 征稿 WeWrite + 三联节气 桌上乾坤 杯中四季 ”
作者:闲云野鹤
2018-03-04·阅读时长4分钟
草木清风生
文/闲云野鹤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这是《茶经》开篇第一句。汉字“茶”上为“草”,下为“木”,中间为“人”,“茶”字可诗意地分解为“ 人在草木之间”——多么清新又文雅的释义。静对一壶清友宛若回归淳朴自然,饮茗之至高也许正是玉川子乘风归去,在草木间与这世界和谐相处以达天人合一境界。
《神农•食经》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可知茶最初是药。汪曾祺先生写茶的功能:“止渴生津利小便与提神。”日本千利休赏茶求“和敬清寂”之道。张宗子“闵老子茶”是以茶会友觅高山流水奇境。欧洲人赞誉:“茶尽管来自东方,毕竟是有绅士气味的。”萧乾说:“英国人最大的享受莫如在起床前倚枕喝一杯热茶。”《陶庵梦忆》中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人多爱茶,对其需求又有不同,但终有一点要肯定,茶不仅限于解渴蠢物,如陈舜臣先生说:“如果口干了,饮水即可,而饮茶除解渴外还有别的目的……这可从中窥见文化的萌芽。”
“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茶文化糅合了儒,释,道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这段话最早是从电台公益广告中听到,后来发现似乎改编自《中国茶经》开篇第一句,读过竟陵子《茶经》又觉得原创应是唐代陆鸿渐,而这位自号“茶山御史”的隐士还有个更响亮的称呼——“茶圣”。其“
六之饮篇”写“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发乎神农”源于“神农尝百草,遇毒得茶解之。”而“闻于鲁周公”是指“周公《尔雅》:‘槚,苦茶。’”东晋西南地方志《华阳国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茶皆纳贡之。”巴蜀向武王进贡茶,说明西南地区在周代已开始人工栽种茶树。
上文的茶话简史从三皇西周跨至唐宋,而魏晋南北朝恰是茶文化承上启下之时,唐裴汶著作《茶述》云:“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魏晋时饮酒文化绚烂,武帝孟德雄心壮志,竹林逸士任性放诞,皆是对酒当歌之激昂慷慨,在太白斗酒为代表的后世,杜康未在文人中式微,但更具精行俭德的茶开始显露身姿成为“饮”中主角。明陈眉公曰:“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类侠,茶类隐,酒固道广,茶亦德素。”西晋张孟阳凭《登成都楼》中“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将“茶”定位于“六清”之上。《三国志》载孙皓嗜酒,宴客每人至少酒七升,不善饮者皆强行灌之,但孙皓体恤老臣韦曜,暗中赐茶代替,这段“以茶代酒”
的典故仿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由“酒”向“茶”缓慢转变的一个重要历程。
晋时饮茶在士族中渐行,但仍未普及,不习饮者称其为“水厄”。《世说》有逸闻:“晋司徒王濛好茶,人至辄命饮,士大夫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洛阳伽蓝记》也记载“水厄”趣事,太和年孝文帝推崇汉化改革,南齐王恭懿投奔北魏,初到北地不食羊肉酪浆,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一饮一斗,号为“漏卮”,此词释义有漏洞的盛酒器,为时人惊叹其茶饮海量。某同僚仰慕之,习茗饮,彭城王元勰对他讲:“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此后北魏宴会虽有茗饮,但鲜卑王爷不满之言迫使守旧派皆耻而不再饮茶,只有降北汉人依旧好之。后南朝萧正德归降,北魏设茗招待,问:“卿水厄多少?”问萧茶量几何,不明就里的正德闹了笑话,答曰:“下官生於水乡,而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水厄”与“阳侯之难”皆可指“溺水”,萧君误解了问题,结果是被举坐之客嘲笑。
王肃投北数年,高祖在宫殿宴请群臣时发现他食羊肉酪粥甚多,孝文帝对此奇怪,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王恭懿应该是想表达鱼羊之鲜虽有优劣,但茶是不能为酪粥做奴隶的,即茶的地位不在酪奶之下。后人凭借此话称茶为“酪奴”,这又是受彭城王戏言误导,君臣对话后,元勰对王肃“神补刀”:“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伽蓝记》描述:“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酒中仙”的豪纵狂放,自唐起饮茶日益兴盛,茶之掌故不胜枚举,值得大书特书是唐时先后出现如陆羽,卢仝,裴汶等茶学大家。陆羽完成最早的茶学专著被尊称“茶圣”,卢仝著《茶谱》被尊为“茶仙”,其“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的《七碗茶诗》为人传颂,据说古时茶坊奉陆羽为师,卢仝,裴汶配于两侧。唐诗浓烈如酒,宋词淡雅如茶。宋朝不求唐时奢美浮华,专注于文化内涵的底蕴深厚。圆悟克勤禅师提出“禅茶一味”。苏轼与司马光茶墨辩论也令茶墨同君子并称并被赋予文雅美德。宋时民间茶肆林立,饮茶的流行至家家户户,如名句“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而《小窗幽记》也云:“寒夜坐室内,拥炉闲话。渴则敲冰煮茗,饥则拨火煨芋。”
明清饮茶已在社会各阶层根深叶茂,《金梅瓶》反映明代市井百态,其描绘饮食之细堪比清代簪缨贵族的《石头记》。明时市井饮茶尚保留烹煮方法,逐渐向冲泡法转变,明人很少饮清茶,多是在茶里掺花果菜蔬煎煮同食,颇有西南吃油茶风格。《红楼梦》言及茶的地方多达二百多处,有名章回如“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妙玉说:“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蠢物,三杯就是饮牛饮驴。”此回中“六安茶”,“点犀乔”,“收梅上雪”等描述透出清时雅士已注重诸如择茶,择器,择水等品茗之法。而比于“槛外人”孤高冷僻,刘姥姥的憨厚则显得亲切可爱,她尝过老君眉后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参看妙玉口中:“隔年蠲的雨水,哪有这样清醇。”这恰巧是劳苦百姓与仕宦小姐对于饮茶的不同追求。
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中写:“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不求解渴的茶也是生活上必要的。又想起亨利•詹姆斯在《仕女画像》中所写的一句话,这话赞美茶简单又明了:“人生最舒畅莫如饮下午茶的时刻。”
(文/闲云野鹤,图来自网络)
文章作者


闲云野鹤
发表文章32篇 获得2个推荐 粉丝53人
人间有味是清欢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