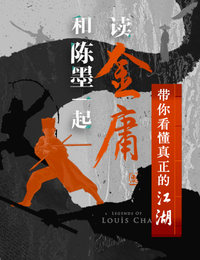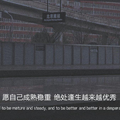2. 为了邀我写《金庸传》,金庸先生分享了很多秘密
作者:陈墨
2019-12-30·阅读时长11分钟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墨。欢迎收听“陈墨说金庸”。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墨。欢迎收听“陈墨说金庸”。
上一次我说到我和金庸小说的因缘,这次我要说我和金庸先生本人的因缘。
我和金庸先生本人的因缘,之前介绍过一段,就是我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读金庸、说金庸,包括跟学校里朋友们一起去谈论金庸,去做讲座以及出金庸的书,那个时候都没有去想到要跟金庸先生去打交道,跟他去联络。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读到钱钟书先生的一句名言,就是“喜欢鸡蛋的人不需要认识生鸡蛋的母鸡”,所以对这些小说的作者的这种兴趣就没有那么大,也没有想到要去跟金庸先生联络。
甚至一开始在1998年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参加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的时候,见到金庸先生我也没有去找金庸先生说话,然后我只是觉得我是严格地按照文本批评的方式去研读他的文本,没有必要去问他是怎么想的,我只是按照我读小说是怎么读的就OK了。在我研究电影和当代电影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时候跟一个导演认识反而会有很多的麻烦,就是他们一定会要我接受他们的意思,从而会压抑了我自己对电影或对作品的这样一个判断和批评。
所以对小说的研究也是如此,尽量地避开作者的干扰,因为我信奉文本主义,就是作品出来之后它就属于公众,作者的这种声音、想法也只是作为一种声音和一种意见而已,然后大家公平地去对待这个文本,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批评意见。
一直到后来同年1998年在台湾中央图书馆中国时报和远流出版公司联合召开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上再次见到金庸,也再次没有跟他去打招呼或者干嘛,一直到还是同一年,好像是1998年在云南大理,《云南日报》的一个记者非常客气,然后他去跟金庸先生见面的时候,说陈墨也来了,然后金庸先生出来跟我打招呼,我跟金庸先生才第一次正式地被介绍认识。 我之所以如此,就是基于一个文学评论的人、学文学专业的人,对文本本身非常重视,然后也不愿意去多打交道。
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在要深入的去研究金庸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认识生蛋的母鸡,让我的想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果你仅仅是喜欢这个作品,甚至仅仅是评论这个作品,不认识这个作者,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研究这个作品的所以然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对作者的成长背景和他的学历背景,以及他自己的个性和心理缺少应有的了解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问题。
在1998年之后的一个阶段,趁我自己在各处去演讲和开会期间,我自己开始收集金庸的一些背景资料。后来远流出版公司出版《诸子百家读金庸》的那一套书叫《金学研究》,1985年最早出版,后来又重新出版,那一套书当中有大量的记者和学者对金庸先生的采访,通过它我了解到金庸先生从小就是一个非常会说故事的人;了解到金庸先生13岁就开始离家,初中的时候就遭遇抗日战争,然后就离家随着学校迁徙,然后甚至他母亲去世他都没有在家里等等;了解到他15岁的时候就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就是《给投考初中者》,以至于他此后三四年的学费,去重庆去考大学的学费都是来自于这本三个初中生编的《给投考初中者》的版税。了解这些事实以后,让我对金庸先生的小说的这种了解,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背景知识和很多的维度。
这里有个小的插曲,就是我后来见到梁羽生先生的时候,因为我写过金庸的评论,也写过梁羽生的评论,然后梁羽生先生就说:“我跟金庸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用一句话来说,不许说多话。”然后我就说,“金庸先生善于经营,您不善于经营,您是一个文人,而金庸先生是一个文人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家,他在小说里面在对故事情节人物都善于经营,然后在小说之外对他的版权和荣誉也善于经营。”
善于经营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从他从15岁编书赚钱,然后到他创办《明报》创办《野马》杂志,后来叫做《武侠与历史》杂志以及他出售《明报》等等一系列的成功的商业案例当中去读,了解到他这个人作为浙江人的一个重要天赋,因为金庸先生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是浙江人”,浙江就做有做生意的这种天赋,了解这样一个文化背景或者地域的文化背景,了解他这样一份才能对了解他的小说创作的构想和经营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但收集那些别人采访金庸先生的材料和我收集到其他的那些档案材料,而且我自己也开始了这种采访,包括我对金庸先生的中学同学,就是浙江农学院的教授沈德旭先生的采访。他当年救过金庸先生,学校转移时他留下来服侍金庸先生,因为当年学校转移,敌人的炮火就追在后面,如果你要掉队了你生死就没有任何保障,然后沈德旭先生就留下来保护金庸,所以他是了解金庸先生的人。
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金庸先生第一次回国的时候,第一个见的人就是沈德旭先生,了解了他中学的情况,然后我还访问了金庸先生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先生,还采访了金庸先生家乡的很多人。这样一些了解以后,发现对金庸的这种传记的了解是对金庸小说阅读的一个必备,研究金庸,不是评论金庸和说金庸、欣赏金庸,就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这些知识或者这些信息是你必须掌握的。所以我的想法就改变了,因为在95年到零几年的这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出版社的邀请我写金庸的传记,哪些出版社我就不去一一的说了,其实我一开始都拒绝了,说我只是研究金庸小说,评论金庸小说,我不写金庸的传记。
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就是最大的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邀请我写金庸的传记的时候,我就说行,因为我当时也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跟金庸先生的因缘比较古怪,古怪的就在于当我不想写金庸传记的时候,我不想去找他的时候他来找我。然后人民出版社给金庸先生写信,说我们想请陈墨来写金庸的传记,希望得到您的同意或者得到您的帮助,因为肯定要采访他或者干嘛的,然后金庸先生拒绝了,他给人民出版社写信说陈墨先生不了解我,他怎么能写我的传记?
这是一个有趣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因为如果不立项去写你传记,怎么可能去深入地了解你?但是如果不深入了解你怎么可能写你传记,这两个是一个话题。我了解到金庸先生他不愿意让我写,就跟人民出版社说:这个没办法,这不是我不写,是金庸先生不让写,但是我的采访和搜集资料工作仍然在进行,市面上出现的金庸的传记,包括香港冷夏先生的《文坛侠圣·金庸传》,大陆的傅国涌先生写的《金庸传》,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小的《金庸传》,我也都收集。
2003年的时候,我已经打消了写金庸传,但是因为要谈论金庸和研究金庸,我得收集有关的资料和信息,要思索金庸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才,怎么能写出这么多好的故事来,我要回答我自己内心的这样一个疑问。但是到了2003年,具体的日期我不是特别记得,就在浙江嘉兴还是在杭州的一个研讨会上,金庸先生来找我,因为在这之前,在杭州我们也见过,在北京也见过,然后我跟张纪中先生见过,跟他也聊过很多,就问他很多这样的问题。
那一年我写过一篇《1959年金庸小说变革和金庸人生的一个重大关键》,大概的意思是一个从传记研究的一个角度,把金庸小说《神雕侠侣》的写作,《明报》的创办和金庸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把这三个事实联系在一起来讨论。然后金庸先生他来找我,就是说希望我写他的这种传记,因为我完全没有准备。当然我也不好意思当面拒绝说我“不”,其实内心已经打定主意不会写,但是跟他跟我说了N多的那些命运,那是外人不可能知道的,包括他见胡耀邦,胡耀邦跟他说些什么话,然后有哪些动作,然后包括他见蒋经国有哪些动作,包括他情感的哪些部分,他其实以为他已经说服我了。
然后他还有三个约定,第一个约定就是关于他的这些政治活动不许公开发表,他会把那些文件档案录音都交给我,让我看让我了解,但是不能够写出来公开发表,这个我能理解,因为它牵涉到海峡两岸的最高领导人,因为他见过邓小平见过胡耀邦见过江泽民见过蒋经国见过那些台湾的领导人,两岸的领导人见面的很多东西要受到档案保密那些限制。
第二条,他谈了他感情的经历和段落,要求也不许公开发表,他的理由就是不要伤害现在的家人,这我也能理解,但是我当时想问没有问出来,因为我决定不去写他的传记,如果要写,一定要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传记要不写感情生活,它就这种价值和写作的内容就会损失很多,然后别人也很难读出来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在当时没有去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记住了他给我的约法三章的二章,就是不要去发表关于他情感纠葛的那一部分,当然还有三次婚姻之外的一些内容和信息。
这两条其实我都能理解,不能理解的是第三条,第三条就是说写完传记以后要经过他审查过目。
这次金庸先生去世之后,我给《明报》一个纪念传记,文章就写了我跟金庸先生的这段古怪因缘,就是为什么会拒绝写他的传记和拒绝以后的一些想法。 他当时提出来,本来我还有一点点松动,因为老人家已经找上来,然后人民出版社也邀请过,我也做了几年的功课,写一写,然后再花两三年时间去做一些更多更细更深入的采访,然后如果能够把金庸先生本人留下的日记笔记档案和那些东西找起来,我再去他走过的地方做一些文献调查和一些档案的调查,能够写出来一部合格的这样一个传记。但是他第三条让我把松动堵起来,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保持传记作者的独立性,没有道理说我写一个人的传记要传主自己来审定我写的合格不合格,那就会影响我对这个人的独立的判断和独立的分析。而我认为自己写作传记的长处除了文献调查,因为我做电影史的研究,文献调查是我的一个功利之外对人的分析和理解,也是我念文学背景的人的一个长处,如果要少了这样一个东西,我就会认为我自己会受到很大的束缚,那这样的事情我不干。
因为这里我就不愿意做,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然可以跟大家交代,当年实际上也是因为自己自信心不够,特别害怕金庸先生那种强大的气场把我给淹没了。
这个下意识当时没有读出来是什么理由,最近这两年才慢慢读出来自己当时给出这种理由只是一个意识水平之上的一个理由,并不是真实的这样一个动机,真实动机是自信心不够,害怕被淹没,因为金庸先生气场实在是比较大,所以对他传记的写作就是这样。后来我正好2004年去美国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是申请到美国的一个学术基金,去做一个电影史研究,然后他追踪又给我来信,然后说要我安排家人和他一起去住他家。 因为当时我没有跟老人家说我不写,不好意思直接回绝,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我以为他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后来他追了一封信来了,他老人家写信是口述,先写成信,然后叫他的秘书把它写成电子版的email,然后发给我,把信的原件也发给我。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商讨写作和采访的计划,叫去他家,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没有打算写传记,而且以后也不打算写,实在很抱歉。我说这个人的机缘就是那样,如果是几年前写了就写了,我说自己的学术计划已经安排好了,最近不太可能抽出时间来去写传记。
这个事实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对这个事实的反省,我今天特别后悔,就是说它三条和几条其实都不重要,如果要有跟金庸先生有50个小时或60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交流,就听他口述自己的历史经历,解释他自己的每一个创作理念,那会给我们这个社会留下一个非常宝贵的,而且是不可多得的、独一无二的一份宝贵的档案,就是金庸先生真正的心声的这样一个档案。哪怕我传记写不写得好,写不好出来怎么样,以及第一版出来经过他老人家把关特别严,然后读起来不怎么样的传记,但我有这一部分录音,录音在那就是一个巨大的财富。特别是我后来做了十多年的口述历史,就是采访中国电影人,就更加后悔就没有去答应写金庸先生的这样一个传记,算是跟金庸先生擦肩而过,从此以后就没有跟先生更多的这种交流。
在杭州在北京在嘉兴,跟金庸先生见到的时候,我也会问到一些重要的问题,包括59年的问题,包括一开始不好问他的那些情感问题,以及他的那些政治态度转变的问题。一开始还只是问小说创作相关的一些问题,包括我提到《天龙八部》段誉很像是释迦摩尼——出家前的乔达摩王子,他的身份、他的表现,以及他整个的路径,我就问他是不是当年参考过或者阅读过释迦摩尼就是乔达摩王子传记,他说没有。我说这是很好玩的事情,因为我读《天龙八部》,读段誉这种阶段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很等等诸如此类的这样一些问题。后面熟了以后,偶尔趁着一些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的时候,我会问一些比较深入一点的问题,但是很遗憾地是,我不能够公开去谈论它,即使金庸先生去世了,因为没有得到他老人家的许可,只能留给以后后人来做。
我对金庸先生这个人的认知是一个曲线,其实我跟金庸先生中间还有很多的曲折。后来朱侠批评我,就是说我得罪了金庸先生N多次,但金庸先生始终没有对我有任何的,包括我当年跟银河出版社签金庸小说评论的系列,版权代理人合同签好了,一叠子合同,后来那个编辑告诉我说,金庸先生在看,我说撤,我说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人都可以编,都可以给我改,只有一个人不可以看,就是金庸本人,就把它撤回来,把那合同给撤掉,这是第一次得罪。
后来包括北京大学的研讨会,金庸先生说点评本只有小学生水平,他说其中的有些只是说好,说这种活小学生都能干,结果把点评的一帮朋友全得罪了,包括冯其庸先生都气坏了。然后后来他还写篇文章,就是陈墨先生、冯其庸先生、严家炎先生他们的写得好,结果把我们搞得里外不是人。总而言之,北大开会的时候,我那些朋友们就说:陈墨,你要去开会,我们就杀了你。 但是严家炎先生来打电话来劝,然后刘再复老师也在海外打电话来劝去开会,我就只好是论文去、人不去,又得罪了金庸先生。我跟金庸先生的因缘,要说的话其实有很多,但是太私人化了,所以不在这说。
今天讲了我跟金庸先生本人的因缘,下次我会谈论金庸到底是什么样人这样一个题目,再会。
如果您喜欢本讲内容
可以随手保存下方海报
分享至您的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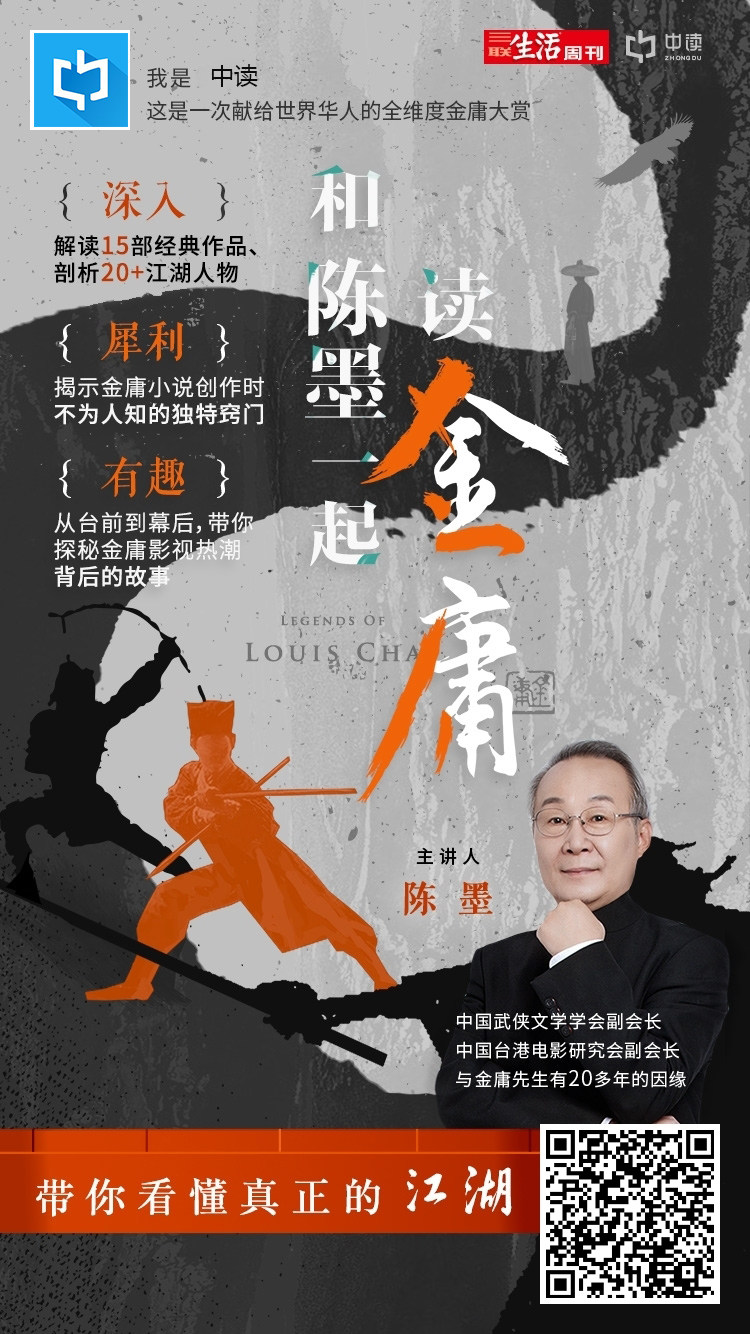
文章作者


陈墨
发表文章99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740人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评金庸系列”十三本等。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