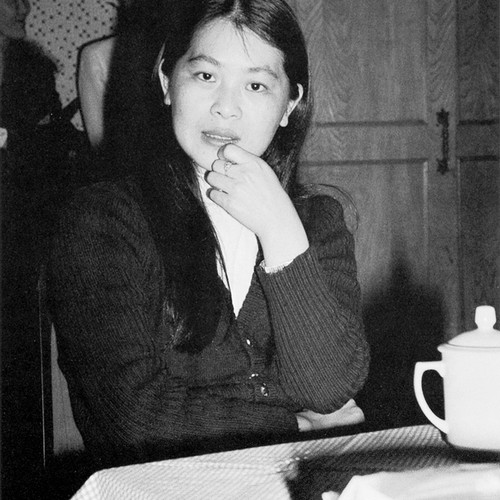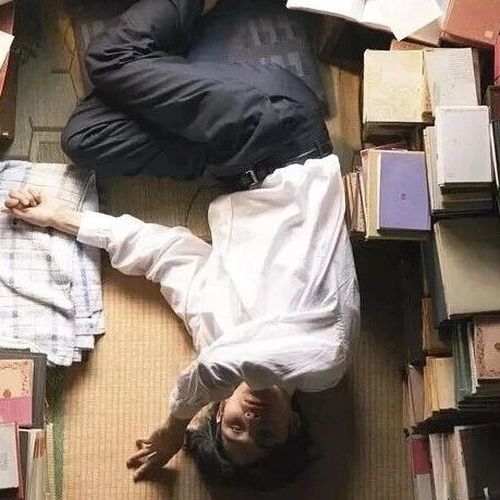通俗小说家茨威格
作者:朱伟
2018-08-13·阅读时长5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2527个字,产生3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 / 朱 伟)
没想到徐静蕾的一部电影,能重新激起很多人对茨威格的兴趣。在我记忆中,茨威格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使“文革”后的第一批文学青年迷醉。当海明威的电报体风行后,他的叙述就已经被大家感到絮叨。他的优秀小说尽管都写于20世纪20年代,但趣味显然还停留在19世纪。
茨威格的小说当然都与张玉书先生的翻译联系在一起,而我们最早被茨威格迷上,却是因《世界文学》1978年第一期发表叶芳来先生翻译的《象棋的故事》。这是1978年2月15日出版的第一期。“文革”后《世界文学》从1977年10月15日起以“内部刊物”的形态恢复双月出版,1977年出版了两期,1978年出版了4期,从1978年10月15日起恢复公开出版。所以,1978年有两个第一期,这是作为“内部刊物”的那一本,所幸它还没有被处理掉,藏在我书柜的深处。从编者按看,此为俄文转译,由张玉书先生根据德文校正。这篇《象棋的故事》当时给大家震撼的是纳粹集中营对一个人精神摧毁的方式——让一个人独自面对空壁,使所有他自己的思想浮现在这空壁中,都变成对他自己折磨的压迫。在这样的窒息中,突出了偶然得到的一本象棋棋谱的作用,它被深深雕刻进了这个人的脑子,占据他思想的全部,然后这个人战胜空无的下棋过程又变成了他自己对自己新的压迫。这完全是把一个文明人变成原始人的过程:文明人面对缤纷的一个世界,能量由此分散。迫使一个文明人变成原始人,只需把他封闭在一个无色的世界里。当能量无所分离,只能凝聚成一个焦点时,就能产生疯狂的爆发力,直至将他自己彻底烧毁。茨威格作为通俗小说家的标志是,他的小说都通过夸张戏剧性来吸引读者。但《象棋的故事》的内核——“最深刻的摧毁是自己对自己的摧毁”却是高于一般思维。这个主题又安排在一艘与世隔绝的轮船上——与象棋冠军的车轮大战引出隐藏的高手,这高手有这样一段精神上毛骨悚然的经历;最后决战,他重新走进那种被封闭的状态,疯狂者还是自己战胜了自己。极端的戏剧化渲染加上一个对人生存哲学思考的内核,现在想在当时它确实足够时髦。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叶先生从俄文转译的这个版本挑起了张玉书先生对茨威格的激情。1979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就推出张先生根据德文版译成包含4篇小说的一个小册子。如果对照叶先生与张先生的译文,以《象棋的故事》的结尾而言,张先生将叶先生的“宽容”改为“宽大为怀”,将“罕见的天才”改为“极不寻常的天才”,文字有些累赘,但把“象棋爱好者”改为“业余爱好者”则突出了象棋冠军的傲慢。张先生译的茨威格,总体说语感很值得称道,那种长句叙述很有抒情气息。我收藏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茨威格小说选》共收有他10篇小说,我喜欢的《象棋的故事》、《马来狂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张先生翻译的有3篇,只有《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个小时》一篇是纪琨译。读惯了张先生译文,读别人译文还感觉别扭。
文章作者


朱伟
发表文章122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1555人
《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