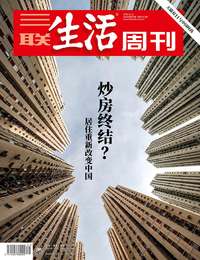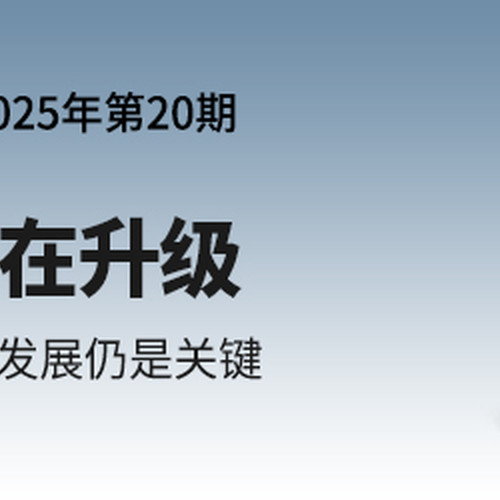最后的“飞虎”
作者:黄子懿
2018-11-08·阅读时长1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429个字,产生1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陈炳靖住在香港沙田区一栋普通民宅内。这位清瘦老人刚满100岁,仍能每日早起走动,更衣用食。约70平方米的房间内,挤着老人夫妇和女儿三人,客厅里摆放着数十件奖杯和照片,墙上挂了一幅巨大的水彩画。画中,一位英俊青年驾驶着战斗机在天空驰骋,远处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
“我的勋章去哪儿了?”最近,陈炳靖时常发出这样的疑问。家中荣誉满堂,唯独少了他挂在墙上的13枚军功勋章。他的记忆中,这些勋章被人拿到北京展览去了,一年多了还未归还。儿子则说,老人是一个月前将勋章冲动地送人了,之后又悔,不停地找寻。
陈炳靖1918年10月生于福建莆田,抗战爆发后报考空军,成为中国首批赴美受训的飞行员,后进入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统帅的、有“飞虎队”称号的美国第14航空队服役参战,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健在的“飞虎队”老兵。那些勋章,记录着他九死一生的人生。
关于“飞虎队”的定义,过往有过小争议。中国飞虎研究学会会长翟永华说,美军第14航空队下,还有1943年10月成立的中美空军混合团。该联队是中国空军,多为中国飞行员,但听美军指挥,美军亦派飞行员支援。“有些美国人并不认为中美联队也是飞虎队。”翟永华说,“但美国飞虎队员都承认,陈炳靖是飞虎队员之一。”
陈炳靖身材修长,一身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军人的烙印深深刻在他身上,这是他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熟悉他的人说,在公开场合,他总是这样,正装配皮鞋,严肃整洁,再拿个公文包,装着老照片和回忆。
直到一年前,陈炳靖还思路清晰,能自行出门,搭乘公交车穿梭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但近一年,他大病一场,身体和记忆都始有衰退。他隐约感到,身体不比从前,反复对记者说:“活了100岁,够了,够了。”似乎,他已做好和同学们“团聚”的准备。当年首批赴美受训的中国青年,有三分之二战死,如今只剩他一人。他对家人说:“等我死了,你们不要哭,要笑。”

受训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陈炳靖当时19岁,正在上海法租界一条商船上见习。他从厦门集美航海学院毕业,原本打算以海为生。但那时,附近海域全是日军,已无法出海。日军从天而降的轰炸,也让租界外的上海千疮百孔。他看见满大街的残肢与尸体,义愤填膺。
“很多孩子的尸体堆在路边,刚放学就被炸死。”往事历历在目。上海形势危急,他和两位同学决定不听家人召唤,改道南京报考空军,期待着上天打日军。他们赶上了中央航校(注:后改名为空军军官学校)12期招生。近三千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报考,其中不乏医生、教师者,最后只录取293人。这仅是初筛,有多半人会在后来的训练中被淘汰。
“当时,选拔的都是出身好、身体条件也好的。”中国台湾退伍空军飞行员、空军抗战史研究者林国裕说。陈炳靖记得,选拔条件中,一个重要标准是外貌,八字眉较受青睐,被认作是勇敢的标识。同期同学中,有台湾作家齐邦媛在《巨流河》中追念的少年恋人张大飞。伪满洲国时期,来自东北的他家破人亡,选择从军。
因日军轰炸铁路和长江运输,12期学员只有搭乘由小电船托载的木船,沿小河自上海、南京到汉口报到,再经南昌、长沙徒步上千公里至成都,接受陆军军官培训。沿途夜宿学校或寺庙,脚底起泡、虱子惹身也毫无怨言。
陈炳靖说,每到夜里,就有东北同学哭着叫妈妈,同学中有7人的妈妈在鸭绿江被炸死。全班人每晚固定唱两首歌,一首国歌,一首《松花江上》。每唱至“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只要一人哭,全班就统统跟着哭。

在成都,他们完成了近两年的步兵训练——这是入学新规。全面抗战之初,羸弱的中国空军不懂陆空协同,作战中曾将中方坦克兵团误伤。蒋介石愤而下令,从12期开始,所有空军学员要接受陆军训练。陈炳靖因而成为抗战中鲜有的、受过海陆空三域训练的军人。
1941年,12期学员从黄埔军校步兵科15期毕业,获少尉军衔。陈炳靖被派到云南继续空军训练。空军淘汰率高,12期共293人,能去云南的仅约100人,其余人转为陆军。而当这100人接受飞行训练时,要全员学飞战斗机。
“到他们那一批人时,空军基本都快战死了。”林国裕说,12期学员从招募起就被寄予厚望。过往,中央航校培养的空军,一半训练轰炸机,一半训练战斗机。到这批学员,被淘汰者才去飞轰炸机。剩余100人中,最后仅约50人升至高级班,有资格飞战斗机。
战斗机飞行中,高空旋转(Spin)是最基础的动作。飞机升到一定高度,直接关掉发动机,在下坠过程中翻跟斗、急转弯、做编队特技。这些都是主教官陈纳德的要求。当时,中国从美苏引进的飞机性能不如日本,天空中,若遇上灵活的日本战机,“这些基础能救你的命”。陈炳靖一边说一边用手打转比画着。一个转弯他稍微快了,头就会疼。着陆后,就会受到陈纳德的严厉批评。
还差一个月毕业、同学都跃跃欲试想上天作战时,陈纳德突然宣布,高级班将赴美国受训,课程与国内几近相同。“为什么还要去美国再来一遍?”所有人怨声载道,无奈军令如山,他们只有乘船被秘密送至美国。
1941年10月,这批学员抵达美国。历时一年有余,辗转美国多地,依然从陆军训练起步,再到初、中、高级班的飞行训练。美方食宿条件更好,有更多的模拟实弹训练。但让他们触动的是,一到美国,陈纳德就让记者来报道。这群在中国已有过训练的年轻人,一上天,就表现出远超新手的技巧,引得美国媒体连连称赞。直到此时,学员们方才理解了陈纳德的良苦用心。“他是想改变当时美国对中国人的偏见,非常伟大。”陈炳靖说。
林国裕说,空军一般有三种情况会停飞:技停(技术不佳停飞)、体停(身体不好停飞)、品停(品德不良停飞)。“而他们当时居然还有‘貌停’,即因外表仪容不好停飞的。”林国裕说,那时能出去的,都是国家精英。
这些因素,都让中国空军在当地很受欢迎。好莱坞明星两次到访,每逢周日,当地女子大学的学生也会邀请他们参加舞会。但学员中几乎没人敢谈恋爱,他们知道,自己的最终归宿,是在生死未卜的天空。“要对得起良心,所有人都不敢谈。”陈炳靖说。
最典型的,莫过于同期赴美的同学张大飞。他为人老实内向,在同学中人缘好。《巨流河》里,张大飞最终没和齐邦媛在一起。陈炳靖说:“张大飞太爱她了,所以不敢娶,怕自己死了齐邦媛痛苦一辈子。”1943年,张大飞同其他女孩结婚,于1945年5月在河南上空殉国。
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激战正酣,他们绕道南美、印度回到国内。作为首批赴美受训回国者,一到国内,就面临着惨烈战事。

文章作者


黄子懿
发表文章76篇 获得32个推荐 粉丝713人
不得拉稀摆带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