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滥用的科学语言
作者:陈璐
2022-04-19·阅读时长16分钟

提到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的名字,人们首先会想到上世纪90年代那个闻名学术界的恶作剧。
1996年春天,美国著名社会与文化研究学术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推出一期题为“科学战争”的专刊,其中发表了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艾伦·索卡尔的一篇论文,题为《逾越边界:关于量子重力学的转化性阐释》。
文章开篇,索卡尔写道:“有许多自然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一直拒绝承认以社会或文化批评为务的学科会对他们的研究有什么贡献,就算有也可能微不足道。若说他们的世界观必须借这种批评的智慧来改写或重建,他们就更不接受了。与此相反,他们紧握启蒙之后支配西方知识图景的长久霸权之教条而不放。”并且通过一系列关于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微分拓扑学和同调,以及流形理论、混沌理论的堆砌和辨析,指出科学知识并非客观存在,而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
谁料一个月后,索卡尔在文学杂志《通用语》(Lingua Franca)上又刊登了一篇文章,宣称此前那篇论文是自己策划的恶作剧。他表示,这篇文章中引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从拉康、德勒兹、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知名学者的著作中抄来,然后随意拼凑的,它们相互矛盾,毫无逻辑,对自然科学的运用更是错误百出。一时之间,大众哗然,这件事很快登上了《纽约时报》《世界报》等报纸头条,引起了西方知识文化界巨大的争论。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的恶作剧”。
次年,针对此事件,索卡尔与比利时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Jean Bicmont)合著出版了《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进一步抨击一些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著作中关于科学的部分,都是些“时髦的空话”。他批判道,这类对科学术语的大量使用反而反映出一种“科学主义者”的心态:视科学为唯一合法的思考方式。
今天,科学被视为唯一合法思考方式的情况似乎变得更加显著,特别是“混沌理论”。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我们看到世界逐渐由秩序走向了无序,经济政治格局呈现出越发复杂多变的状况,人们的内心也对未来将走向何处充满了迷茫。新冠疫情就仿佛那只扑闪着翅膀的蝴蝶,激起了一连串的效应,彻底从方方面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面对这样的复杂情况,前沿跨科学领域的混沌理论和复杂系统,似乎成为通向理解这个无序世界的新道路。混沌经济学、Covid-19的时间动态复杂性……生命科学、医学、经济学、政治学都试图用这门新兴学科研究、了解当下的状况,并对未来做出预测,各种与之有关的术语和公式也随之被放到公众面前。但就像索卡尔所批判的一样,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早在1997年撰写《时髦的空话》时,他便批评了人文学者语义暧昧地使用混沌理论的术语描绘历史和社会主张。2013年时,他还公开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和马西亚尔·洛萨达(Marcial Losada)滥用洛伦茨方程得出“科学结论”的问题。洛伦茨方程已成为混沌理论的经典,也是“巴西蝴蝶扇动翅膀在美国引起德克萨斯的飓风”一说的源始。科学被滥用的情况是否有变好?我们该如何识别这些科学陷阱?我向索卡尔邀约,想跟他聊聊这个问题。以下是本刊对索卡尔的专访。
混沌理论的误用
三联生活周刊:多年来,你其实一直在持续关注人文社科领域对自然科学知识滥用的问题,2013年还针对一篇被引用次数很高的积极心理学论文,对其中运用洛伦茨方程的数学问题进行了批判,可否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艾伦·索卡尔:2011年11月,一位名叫尼克·布朗(Nick Brown)的学生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他是伦敦另一所大学积极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邮件的内容很有趣,布朗发现在积极心理学的同行评议期刊上,有篇论文名为《积极效应和人类繁荣的复杂动态》(Positive Affect and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Human Flourishing),作者是心理学家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和马西亚尔·洛萨达(Marcial Losada)。弗雷德里克森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几项著名心理学奖的得主,而洛萨达是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前主席。他们都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在这篇论文中,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基于洛伦茨方程的一个非线性动力系统模型,得出结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理想比例为3∶1,或者更准确地说,是2.9013∶1。弗雷德里克森还在随后面向普通读者的《积极情绪的力量》一书中普及了这一观点。这篇论文是积极心理学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大部分基础建立在洛萨达1999年在《数学和计算机建模》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高绩效团队的复杂动力学》之上,而洛萨达这篇文章让布朗也感到存在很多问题。布朗向我表示,他认为这些文章似乎是类似的“知识的骗局”,“这让我开始感到不安”。
一开始我几乎忽略了这封电子邮件,三个星期后才重新发现了它,于是我联系了布朗,并通过邮件跟他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合作。这是段很有意思的经历。2012年我们完成了论文,向学术期刊《美国心理学家》寄出,最初他们并不想发表我们的文章,但我在邮件里告诉他们,如果拒绝考虑这篇文章,对他们来说将很尴尬,因为我会将文章投到别的地方。或许因为我已经有些名气,这点当然很有帮助,所以最后他们还是把文章发给了审稿人。审稿人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而我们一一回答了,并做了一些小的修改,2013年最终发表了它。
后来,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撤回了他们论文的一部分内容,但从他们的撤稿中看不出来他们到底撤回了什么,没有撤回什么。这也是我们在后续发表对弗雷德里克森的回复时提出的一个观点,即不清楚他们所声称的内容是否仍然有效。无论如何,我们试图在我们写的那两份后续文章中解决所有这些疑问。从那时起,弗雷德里克森就没再多说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可能只是想忘记这件事,然后继续她的积极心理学研究。洛萨达也没有再提及此事,但确实后来仍然经营一家基于这个洛伦茨方程理论的咨询企业,不过2020年时他去世了。
实际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我们的文章,又有多少人仍然相信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的理论,我也不知道积极心理学界到底产生了什么反应,不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放弃了这一理论,或者他们是否只是想做出最低限度的错误承认,然后继续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但我认为我们的文章确实有一些影响,相当多的人确实读了它。
在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这个案例中,其实涉及的是一种更传统的对科学的滥用。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们走得太远,总是试图变得更加数学,对数学和物理学进行了一种不同的滥用。他们两人的这篇文章是积极心理学这个心理学子领域中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但在布朗之前,没有人发现问题,我认为这是相当惊人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篇积极心理学论文主要利用混沌理论中的方法和公式。混沌和复杂系统这个前沿的跨学科领域,确实常被认为是未来理解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大门。在你看来,当我们看到这类使用了混沌理论的社科文章时,需要识别的主要陷阱是什么?
艾伦·索卡尔:首先我想说的是,“混沌理论”是口语化的名称,它的技术名称应该是一种数学理论,即“非线性动力学”。关于非线性动力学,我认为可能会出现两种预期应用:
比如像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他们试图将非线性动力学应用于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他们真的在试图使用这些方程。这种应用可能是正确的,但需要严格的证明,正如我们在论文中详细解释的那样,你必须做很多事情来证明在应用中使用非线性动力学的有效性。然而所研究的系统越复杂,就越难以给出这些证明。因此,无论是物理学、化学,或者在种群生物学中,非线性动力学的大多数有效用途都是发生在简单的情况下;而在社会科学中的有效应用,并非不可能,但这很难。
实际上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争论,经济学是否有案例可以有效应用非线性动力学。如果说有社会科学领域可以应用到非线性动力学,可能就是经济学。比如著名的“猪周期”。农民在猪肉销量多的时候养了大量的猪,这些猪被宰杀后,大量的肉流通到市场被出售,所以猪肉价格下降。当猪肉价格降低时,农民认为明年不该养那么多猪,所以第二年他们又养了太少的猪,于是猪肉的价格又上涨了。因此,原则上猪肉的价格存在两年的振荡周期。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可能适用于这样的简单现象。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并不是真正试图应用非线性动力学的数学理论,而只是用这些理论或者术语来做比喻,比如谈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或者他们称之为“蝴蝶效应”的想法。因此,有时你会看到这些自然科学理论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参与到所有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但通常它并没有增加任何细节去证明这种应用的合理性。
三联生活周刊:我确实注意到,在《时髦的空话》中你探讨的滥用更多是一种词义混淆,比如把科学中关于“混沌”“线性”“非线性”“不可预测性”这些专业术语的语义与生活或者其他场景中的语义加以混淆;但你在2013年针对积极心理学这篇论文的批评中,这种滥用指向套用公式,设置不严谨的实验以便赋予其结论某种科学性。
艾伦·索卡尔:正如我前面所说,我认为有两个不同的群体。弗雷德里克森是一位心理学教授,她试图让自己的工作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科学。他们用实验和统计数据来写论文,声称要把数学应用于心理学,却没有构建真正的数学理论模型,就像我们在书中批评的一样,他们试图做的更多只是在抛出文字,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威慑。
另一批人他们没有试图成为科学家。就像在《时髦的空话》中讨论的那些人一样,使用科学词汇也许是为了试图使模糊的想法看起来更深刻,但不一定更科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读者不是数学或物理学专家,他们可以抛出这些花哨的词语,假装他们知道这些自己并不真正知道的东西,而他们的读者也不会意识到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因此,我认为这两个群体彼此隔离。例如,我相当肯定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从来没有读过这些法国学者的书,或者他们读过,但也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另一方面,那些法国学者我怀疑他们是否读过任何关于混沌理论的任何版本的数学著作,他们只是听说过关于混沌理论的只言片语,没有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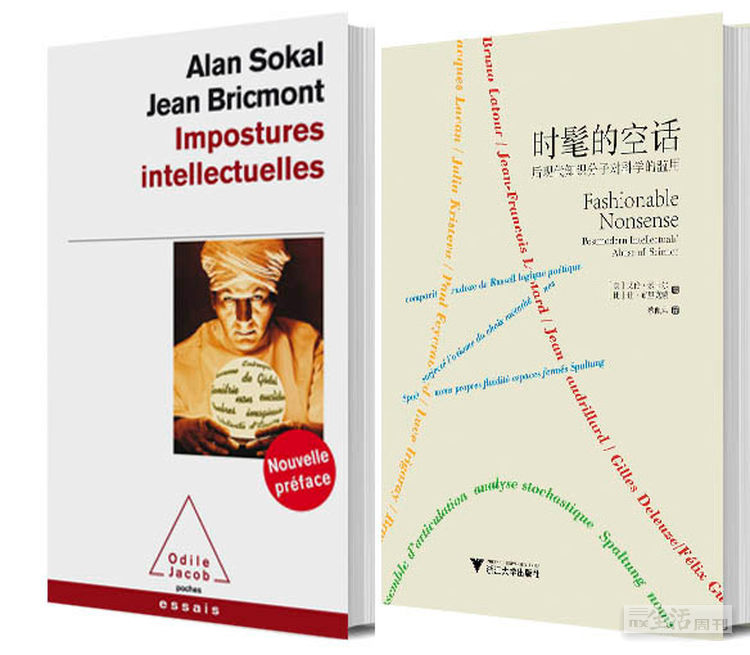
“房间里的大象”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为什么会是尼克·布朗,一个非全日制的在读研究生提出了这个问题?
艾伦·索卡尔:我不确定,也许正因为布朗刚开始在这个领域工作,作为一个局外人更容易持有怀疑的态度。而且他不是一个典型的学生,他已经45岁了,有自己的事业,在20多年前的大学生涯里学习过不多的数学知识。他告诉我,最开始他学的是工程学,后来放弃了,因为数学对他来说太难,所以改学了计算机科学。但他显然已经拥有足够多的数学知识来批评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的文章。大概55岁时,他取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并从那时起做了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又一次提高了心理学的严谨性标准。他和他的团队写了个计算机程序,用来测试心理学论文中是否存在不可能的数据。这是什么意思?想象一下,如果你有10人的样本,然后问他们一些问题,结果你说73%的人回答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10个人来说,这个数据必须是10%的倍数,不可能存在7.3个人,对吧?所以他们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从心理学论文中提取数据表,搜索不可能的数字,他们的确在一些人的论文中发现了很多不可能的数字。
如果出现少量不可能数字,可能意味着你在将数据输入电脑时很马虎,或者你本身很马虎,但他们有时会发现来自同一批人的大量不可能的数据以及重复的论文。他们还发现了一些被认为是欺诈的案例,有人编造数据,论文完全是编造的,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数据,而全是一些被创造出来的不可能的数据。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自然科学知识被滥用的现象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被忽视?
艾伦·索卡尔:长期以来,数学或物理学在其他领域被滥用的现象一直存在,有时也会遭到批评。我认为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发表了针对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的论文质疑后,除了作者本人,我们只收到5位来自积极心理学领域专业人士的评论,而且他们都不是这个领域的“大人物”。“大人物”或许在保持低调、隐藏了起来,既不想发表任何关于他们朋友的负面评论,也不想为之辩护。
《时髦的空话》刚出版时,我们收到了一些学生的电子邮件,他们表示感谢,并告诉我:“我读到这些东西时没有理解,以为自己很笨。现在我意识到,我没有理解它们,是因为它们不可能被理解,这些东西甚至没有任何意义。”但那是25年前的事了,我不知道现在新一代的学生怎么想。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新一代的学生是否在读我们的书,或许没有。
三联生活周刊:最初你为什么会关注到人文社科领域对自然科学知识滥用的问题?
艾伦·索卡尔:我一直对社会科学以及社会和政治问题感兴趣,但发现“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社科领域滥用自然科学知识的具体问题,是在阅读了生物学家保罗·格罗斯(Paul Gross)和数学家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的一本合著后,书名是《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1994年以英文出版,但直到2019年,初版发行25年之后才有了法文版。他们邀请我为这本书的法文版写了一篇序,我在这篇序里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具体的故事。
最初看到这本书,我的想法是:“又是一篇右派的言论,说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危险分子如何占领了大学,对我们的孩子进行洗脑。”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美国,一连串这样的哀叹很常见。但接着我又想:“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我是一个学术左派,但从没产生过关于科学的任何争论。”
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人文社科学界有了一种小而时尚的亚文化,转而对科学及哲学进行说教,把两者都搞得一塌糊涂。这些人包括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家、社会结构主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以及新潮的“文化研究”实践者、“女权主义认识论”和“后殖民理论”的倡导者。与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为民运动或者70年代的女权运动不同,这些学者认为,物理学、化学、天文学以及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包含了西方的、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旨在为“其他认知方式”辩护,认为它们“同样有效”。
因此越来越明显的是,物理“现实”与社会“现实”一样,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科学“知识”远非客观,而是反映和编码了产生它的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科学的真理主张本质上是充满理论和自我参照的;因此,科学界的话语尽管其价值不可否认,但对于来自异己或边缘化社区的反霸权叙事来说,不能宣称拥有一种特权的认识论地位。
读完《高级迷信》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图书馆,查阅格罗斯和莱维特引用的一些书籍和文章,看看他们的批评是否公平。也许他们断章取义地扭曲了作者的真实意思,从而使一个合理的论点,或者至少是一个值得辩论的论点显得很荒谬;也许他们引用的是小人物发表的愚蠢言论,但忽略了同一意识形态阵营中的主要人物所做的扎实工作。最后我得出结论,在大约80%的情况下,格罗斯和莱维特的批评是正确的:这些文本和他们说的一样糟糕,甚至在少数情况下更糟。剩下的20%,格罗斯和莱维特似乎有所夸大:这些文本确实很平庸,但他们描绘得比实际更荒谬。
所以基本上,我提出问题的动机既是知识性的,也是政治性的。首先,知识性动机涉及两方面:科学的滥用,以及我认为被误导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思想。在书中你可以看到关于这两方面的体现,个别章节我们谈论了科学语言的滥用,随后有关“知识相对主义”的长章节,我们解决了一些科学哲学思想的问题。其次是政治上的考虑,这股新思想潮流在美国和英语世界的左派阵营中出现,而我个人的政治倾向属于左派,所以我很失望,我们政治上的朋友们正在犯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不仅是智力上的误导,对我们支持的政治事业也是有害的。
我们非常努力地把这两个动机分开。在书中,我们试图解释说,知识论证应该在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评估,你不应该因为喜欢我们的政治理念而接受我们的论点,也不应该因为不喜欢我们的政治理念而拒绝我们的论点。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这本书1997年首版时法文原名为“impostures intellectuelle”(知识的骗局),1998年美国出版时改为了“fashionable nonsense”(时髦的空话)。书名的改动背后是否有什么特殊考虑?在法语和英语国家是否掀起了一些不同的讨论与关注?
艾伦·索卡尔:改变标题的原因实际上不是那么重要。英语中“impostures”这个词非常不常见,几乎不怎么被使用,因此在美国出版时,我们将书名改为了《时髦的空话》,我们认为这对英语国家的读者来说更容易理解。不过有点复杂的是,《时髦的空话》是为美国和加拿大出版的。我们还有个为英国和其他英语地区出版的英文版沿用了《知识的骗局》这个书名,原因是这本书在法国出版后,记者已经写了很多文章,英国出版商因此建议我们应该保持相同的书名,人们会知道这是同一本书。所以这有点好笑,这本书的英文版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取决于你读的是美国版还是英国版。
这本书确实在不同地区引起了不同的讨论。在法国,人们讨论的主要是书中那些法国知识分子滥用科学语言的部分,因为我们所批评的这些知识分子在法国非常有名。他们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有时还出现在电视上。但在美国和英语世界,关于知识相对主义的章节引起了更多讨论。我想是因为其中关于哲学和政治的部分在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关注。普通的美国人,即使是一个每天阅读《纽约时报》的美国人,或者美国的物理学或数学教授,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书中批评的这些法国知识分子是谁。
“索卡尔的恶作剧”27年后,一切都变得更糟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否关注到,2017年有三位学者海伦·普拉克罗斯(Helen Pluckrose)、詹姆斯·A.林赛(James A.Lindsay)和彼得·博格西安(Peter Boghossian)也编造了20多篇毫无意义的文章试图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截至他们公开自己的“骗局”前,其中已有7篇被有着同行评审机制的严肃期刊接收,另有7篇处在评审阶段,仅6篇被拒绝发表,其中政治正确的文章似乎更容易被发表。这看起来是对你的模仿与致敬,我很好奇你如何看待他们这次的举动?
艾伦·索卡尔:在普拉克罗斯加入前,林赛和博格西安其实发表过一篇论文《作为社会建构的概念性阴茎》(The conceptual penis as a social construct)。我当时对此写了一篇评论,批评这篇文章虽然非常有趣,但并没有证明太多东西。我想他们也许把这个批评放在了心上,决定构建更大和更仔细的实验,不是写一篇文章,而是写了20篇,这非常有趣。
如果我来玩这个恶作剧,我会把任何一个学习过数学和物理学的学生都能立刻看出来是胡说八道的东西放进去。这是种测试。我的文章旨在模仿我所看到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并故意做得更糟。但林赛和博格西安的文章并没有比他们所模仿的文章差那么多,他们更多是想表明写这些差文章并让它们发表是多么容易。所以,也许他们所证明的与我所证明的有一点不同,因为他们的文章不是那么荒唐,或者至少不比他们模仿的那些人更荒唐。
三联生活周刊:有观点认为,正是因为各学科专业化壁垒的不断提高,导致公众对于来自陌生领域的词汇及话语时常采取一种听之信之的姿态,而这种隔阂加剧了科学知识被滥用的情况。
艾伦·索卡尔:我不知道。但普拉克罗斯、林赛和博格西安这次行动其实指向了人文社会科学里,特别是西方世界里一个日益政治化的角落,他们称之为“申冤型研究”(grievance studies)。因此,这可能与以下事实有关:在这些领域,政治考虑变得比智力考虑更重要。我在对他们第一次的批判文章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我没有回答。
三联生活周刊:尽管你在《时髦的空话》的结尾有着美好的期盼,希望出现一种知识文化,“是理性主义而非独断主义、心态是科学的而非科学至上的;心胸是开放而非轻浮的;政治上是进步的而非党同伐异的”,但许多人认为现实中,20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在变得更加糟糕。
艾伦·索卡尔:是的,我认为事情正在以一种不同于我所预料的方式变得更糟。普拉克罗斯、林赛在做了这场实验后,与我们做了类似的一件事情,就是写了一本严肃的书来试图解释骗局中的一些问题,叫《愤世嫉俗的理论》。我在给法译本写的序言里解释了,事情是如何以我没有预见到的方式变得更糟糕的,知识的混淆以何种不同的方式变得更加嵌入政治辩论中,特别是在英语世界。在美国和英国,很多政治辩论,特别是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跨性别权利以及种族主义,很多后现代主义思想都已经被使用,但与原来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也许更危险。
文章作者


陈璐
发表文章77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258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