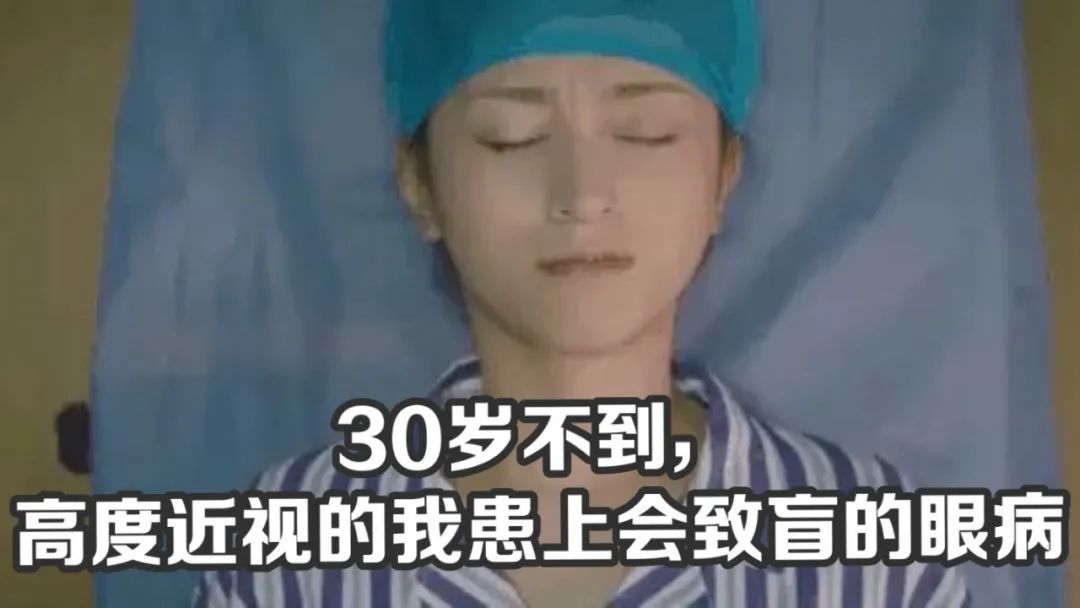在川西深林里,为野生大熊猫捡屎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30分钟
记者|黄子懿
图|张雷
“捡屎官”
4月上旬,位于四川雅安界内的泥巴山刚刚转暖。这是一片横亘在川西高原东面的大山,呈东西走向,属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大相岭山系。山顶的积雪终于融化,露出了它让人惊叹的一面:向阳的南坡是高山草甸,还裸露着块块黄土,北坡却是树木葱郁、云雾缭绕,宛若自然界的阴阳两界。
这是一道川西的气候分水岭,一条108国道像是一把蜿蜒的长矛,径直插入了这个气候阴阳界的中间。4月8日下午,大相岭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的科研监测股股长宋心强和八位队友一起,来到泥巴山保护站做2025年的首次春季巡护。保护站紧挨108国道一处下坡弯道,海拔1800多米,两层的宿舍楼在大卡车路过时会有一种轻微的震颤。在经历了一个无人的冬天后,本就老旧的小楼又多了一丝破败,觅食的野老鼠们拥来翻捣,咬坏了几乎所有电线和插线板。“太疯狂了,它们显然把这里当家了。”宋心强到站后第一件事,就是和队友花了一天打扫,好不容易才把冰柜电线给接上了。
冰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要拿它来冻各种各样的屎。宋心强打开冰柜,给我看春巡第一天的“战果”:几坨豹猫屎,看着跟普通猫屎无异;一根白腹锦鸡的羽毛,它在繁殖季后会尾羽脱落;以及更重要的、也是本次巡护的主要目标——熊猫屎。它个头很大,纺锤状,远观像是一个饱满圆润的红薯,近看是由一根根被消化的竹节黏合而成,有一种油亮的绿色和竹子的清香。这让一坨熊猫屎在野外十分好辨认。冰柜冻着新鲜的屎,饭桌、办公桌也放着几坨装袋的还未入柜,“有时候我们在饭桌上吃饭,中间是一盘菜,旁边就放的全是屎”。

野生大熊猫在我国的大熊猫数量中占据了大多数
“一般最好是三天以内,超过七天就不行了。”宋心强说,大熊猫由肉食动物进化而来,肠道短、消化快,一般进食四五个小时就会排泄,“有时候边走边拉,边吃边拉”。第一天巡护,队员找到的最近一坨屎离保护站直线距离不到200米。宋心强专程带我去看,那是108国道边一处需要躬身前行的竹林平地,还残存着4~5坨已晒干未拾捡的粪便,咬节长度3~4厘米,目测是一只成年大熊猫,“幼猫屎会比这个小很多”。
我望着这几坨屎,听着国道上川流不息的卡车行驶声和喇叭声,很难去想象,就在不久之前,居然有一只大熊猫偷偷跑到离人类如此近的地方,悠闲地躺着吃了大半天竹子。
这或许是一份属于雅安的特性。雅安是四川盆地通往川西高原的一大入口,境内绵延的群山中就有中国最早发现大熊猫的地方。上世纪60年代,国家成立卧龙、王朗等首批自然保护区开始保护野生大熊猫,但雅安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汉、藏、彝等不同民族聚集,一直面临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大熊猫的粪便里残存着大量竹节和它的“身体密码”
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成立,雅安有近40%的面积都在国家公园内,荥经县更是有近50%。108国道上的泥巴山不仅是气候分水岭,也连通着荥经与南部的汉源、石棉县城。我来到这里,就是想看看在一个人类活动频繁且不可避免的地方,是如何做野生大熊猫保护的。
当然,这一切都要从寻找一坨熊猫屎开始。那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宋心强这样给我打预防针:一方面,大熊猫喜爱高寒环境,生性警觉,嗅觉、听觉都在人类之上,“你靠近它前,它早就发现你,躲起来了”。另一方面,巡护监测对体力要求极高,之前也有一些媒体、团队想要跟队,但“根本坚持不下来”,耗到后面只好找地方摆拍了事。不过他还是答应,让我们跟一条短距离的常规路线试试,“顺利的话早上8点半出发,中午12点前就能回来”。
“别指望能遇见大熊猫。我追了七八年都没见着一只,屎倒是捡了一大堆。”宋心强自嘲道。
找屎之旅
次日9点,一辆柴油皮卡车蜿蜒着下山,在108国道的一个路边把我们放下。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情况有所不妙。
来到泥巴山前,我以为这趟旅程就像小众徒步路线,是带着山林野趣的,即使耗费体力,但至少也是有山路或小道可走的。但下车处目之所及,只有国道下方一条融雪涨水的小溪,身后是一个小山坡和一座绿荫葱茏、呈阶梯状的大山。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爬上大山,查看布置在高处的两台红外相机、更换电池和存储卡,并在沿途收集一切有价值的动物残留物。
少年时期,我曾多次路过川西高原的这些大山,想象着这些充满压迫感的山体深处会是何等野性,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会亲自来一探究竟。现在,摆在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这里压根没有路,我要怎么爬上去?溪流还涨水了,要怎么跨过去?
领队者是生于1996年的队员杨稀,带着两位生于1998年、2001年的队友,他们年轻,身手灵活。他看出了我的犹豫,让我跟着他扯着竹子、树干下到溪边,再踩着几块大小不一的石头跨过水流。他的动作一气呵成,而我仅是翻越一块大石头,就在大腿根处感受到了久未有过的韧带撕扯。同行的摄影师张雷为了跨过这条溪,更是在岸边徘徊了十几分钟。后来他告诉我,一下车看到是要这样爬山后,他就知道自己肯定要放弃了,“只是什么时候的问题”。

在108国道边的一处密布竹林里,宋心强(前)与队友们发现了一堆熊猫屎
跨过溪流后,我们继续跟着杨稀翻上一个陡峭的小山坡。不过20多米的高度,却要手脚并用,紧抓长满苔藓的树干、树枝和竹枝。山坡的平缓处是一片低矮竹林,需要我们躬身前行,身前的巡护队员边走边扒拉树枝,不时用镰刀在丛林中开出一条路来。我身居其后,时刻留心躲避他们扒拉反弹过来的竹枝或树枝,也谨防镰刀的误伤。茂密的丛林里一不留神就可能落单,因此人要时刻呼应,发出猴子一般的吼叫。
杨稀毕业于西华师范大学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2017年来到大相岭自然保护区工作。他戴着一副眼镜、挂一个相机,话语间有股理科生的严谨与斯文,但在山里他行动迅速,留意林中一切有价值的动物残留,有一种属于丛林的文武双全。仅是在这个小山坡上,我就收获颇丰,先是遇见了一只草绿龙蜥(四脚蛇),然后又在一个空地处发现了一个乱糟糟的野猪窝。曾有一只野猪咬下了周边竹子和树枝,在这里搭起了一个有入口的巢穴。“它要用这个来保暖,尤其是母猪产子的时候。”杨稀解释。遇到这些时,队员们都会拍照,把小动物或其残留物装袋留好、系在树上,返程时取回。
而返程还遥遥无期。再往深处是一个山沟,有一条水量更小的小溪经过。相较于国道边的水流,山沟里的更加原始,树荫遮蔽,涉水的石头上布满了苔藓,我在踩着石头过河时不慎滑了一跤,打湿了左腿。此时,望着山沟一侧还有一个目测超过70°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坡,满头大汗的摄影师张雷终于选择了放弃,留在原地等我们。我则继续跟队,开始了一段强度更高的爬升。
这是一个更加考验攀爬能力的过程,因为坡陡,人要按照“之”字形爬升。手抓着树枝和竹枝借力的时候,脚上还要不断地寻找着力点,那可能是一窝竹子,也可能是半裸露在山地之外、不知道有多大岁数的老树根。潮湿的气候下,布满枯枝败叶的腐殖质层也是松动的,需要斜着身子反复踩实。费力爬升时,我还得担心滑嫩的树枝或腐殖质层里是否会突然蹿出来一些莫名生物。
在这样的原始山坡上,我此前不多的户外经验完全无用——登山鞋的鞋底很硬,踩到苔藓极易滑倒,还不如穿一双劳保鞋轻踩通过。登山杖更是毫无用处,远不如镰刀或一副厚实耐造的手套。唯一有用的是冲锋衣,它的外壳和帽子给人一种被包裹的安全感,让人能在丛林里埋头前行,以及队员们教我下载的一个户外App。终于爬上山脊后,我喘着宛若刚跳完HIIT一般的粗气、感受着咚咚心跳,从兜里掏出了许久无法顾及的手机:爬升约一个半小时,海拔上升不到200米,却消耗了1016大卡。这应该是城市生活能在这里提供的唯一经验了。

丛林里也有城市难以想象的危险。山脊上有此行要查看的第一台红外相机。“山脊相对平缓,野生动物喜欢沿山脊活动,更加节省体力。这里视野也更好,一眼能望去20多米,能拍到的东西更多。”杨稀说,危险也是在此频发的。曾有队员遇上了黑熊,拿着树枝吼叫才把黑熊驱赶走——黑熊又跑到了其他队友的区域。还有一次,两位队员撞见了野猪一家,两边悬崖耸立,两人只好立马爬上树、屏住呼吸,等野猪靠近大吼大叫才把它们赶走。这种来自人类的威慑对群居的猴子则毫无作用,如果狭路相逢后人类扔树枝和石头来硬的,一群猴子会立马加倍奉还,所以最好的方式是遇见就跑。
小体积的生物更加可怕,那是一种在人类注意力之外的无孔不入。山上最常见的是蚂蝗和蜱虫,队员们在爬上山脊后会相互检查。蚂蝗一旦感知到风吹草动就会扑上来吸血,人毫无知觉。曾有一位队员在巡护回站后,晚上就寝前才发现整条内裤全都是血,有两只蚂蝗正在裆里吸得畅快。蜱虫危害更大,它附上人体后会顺着身子爬,找好地方后会把带着病菌毒素的鼻头扎入人体,极易引发人高烧和感染。“那真是防不胜防。有时候你白天看着没事,晚上睡觉时把衣服放在旁边,它就有可能顺着衣服爬到你身体上来。”杨稀回忆,一位队友连续两次被蜱虫爬入鼻孔,第一次没经验高烧不退,去医院抢救时才发现蜱虫已经长得很大了。
讲完这些故事后,杨稀顺水推舟地劝我放弃,因为要抵达第二台红外相机处还有一段漫长的高强度爬升。我汗流浃背地喘着气,表示同意。但看着两位队员继续往上的背影,我也意识到,放弃是我们这些外来者的特权,如此消耗与高风险的巡护却是他们的常态——季度巡护每三个月就要展开一次,队员们要在一个多月里爬完荥经片区860公里内的440个网格点位,查看并更新对应的440台红外相机。在远离108国道的更深处,没有水、电和手机信号,巡护队员要请向导,背上一两周的物资,夜宿在废弃水电站的危楼里围炉取暖,或是砍下木头、拉着塑料布搭起帐篷,在寒风中通铺就寝,哪怕是男女同行。如果说生物圈的危险还可以规避的话,那自然界的风寒就无法阻挡了。常年在阴冷的高海拔处行走,让几乎所有队员都患上了风湿,一下雨就腿疼——包括2001年出生、走在我们前方的最小年龄队员康峻。
一个多小时后,康峻和队友凯旋的簌簌声从丛林里传出。他们带回来了一坨大熊猫粪便与拍到的珍贵影像。一只大熊猫在海拔2300多米的山上对红外相机展现出了无尽好奇,它扒拉相机的画面成了这个相机的最后影像。队员们还带回来了路上被几只猴子扔树枝围攻的笑谈,以及正在墨绿色的制服上游走乱窜的几只蜱虫。杨稀赶紧帮队友清理,把捉住的三只蜱虫用塑料袋封好,打算以后做科普用。然后,我们一行人连滚带爬,回到了108国道的溪流边。时间是下午2点。
后来我才知道,这条路线是巡护队招募队员时一条常规的考试路线。从108国道边爬到山脊上的第二台红外相机处,24岁的康峻能用56分钟往返全程,而手机App显示,我只爬了约2/3的路程,海拔波动不到200米,却耗时超4小时,消耗2100大卡。
孤岛化:大熊猫保护之忧
巡护当天,宋心强没有跟我们走,而是走了一条更远更高的路线,“我要去碰猫”。2024年初,泥巴山高处拍到了一只大熊猫母兽带崽的画面,他想看看今年能否在相应区域捡到粪便,甚至碰见这对母子。下午3点多,他带回来了几坨不算新鲜的粪便,也没有遇见熊猫,言谈间有些失落。
能否在野外遇见大熊猫,是巡护队衡量自身工作的一道尺。大相岭管护中心里,几乎每个人都会说自己从没在野外见过大熊猫,其他人也没见过。为什么要如此执着于遇见野生大熊猫呢?跟着队伍进行一趟巡护后,我似乎能理解他们一些:作为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偶遇大熊猫不仅是一种期待和认可,也代表着一种回报。
巡护工作不仅高危,也很寂寞。队员们三两成行,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外风餐露宿,阴冷高寒的天气对于外地人尤为难熬。宋心强来自平原地带的山东济宁,硕士是在云南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2017年来到这里做野生大熊猫的监测保护,不仅患上了风湿,每次见面同学都戏谑说他皮肤白了不少。常年的巡护中,他还养成了野外摄影的爱好,在工资不多的时期就自掏两三万买了相机和镜头,八年来在丛林里留下了不少穿梭的划痕,“我得给自己留下一些印记,让这些年的工作没有白做”。

巡护队员们要在四川这些崎岖陡峭的山体中协力攀爬
这些寂寞的付出背后,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要遇见大熊猫,最近可以去60公里外的雅安碧峰峡,再远可以去都江堰或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为什么又要成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呢,为什么又要去国家公园里偶遇野生大熊猫呢?
原因在于,相较于圈养大熊猫,今天的野生大熊猫仍是需要保护的,它们代表了中国大熊猫的大多数。截至2024年11月,全球大熊猫圈养数量有750余只,而早在10年前,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就显示,中国有1864只野生大熊猫活跃在川、陕、甘三省。这一数字是靠着抽调的巡护人员“捡屎”三年才完成的,比40多年前的1100多只数量大幅增加,彰显着中国在保护大熊猫方面的成就。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就将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
但隐忧在于,这1864只野生大熊猫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有灭绝风险。原因是大熊猫种群的延续依赖于遗传基因的多样性,长期圈养已被证实有近亲繁殖的灭绝风险。野生大熊猫多年的生存演进则是靠着不同种群、谱系之间的交流和繁衍来实现的。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熊猫的栖息地变成了一个个“孤岛”,它们之间自由的“走婚”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零散破碎。这已经威胁到了其基本的生存规律。比如前述调查就显示,1864只野生大熊猫可被分为33个局域种群,有24个小种群都有较高的灭绝风险,数量占12%。有鉴于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2015年数据公布后表示:大熊猫生存形势依旧严峻,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从地图上看,大相岭是与邛崃山系相连的,二者在川西高原入口呈一个微微右倾30°的“L”形交会,邛崃山系就是那根很粗的竖画,有超过500只野生大熊猫,而大相岭山系则是很细的短横。泥巴山位于二者夹角的下方,是两大山系大熊猫“走婚”交流的一大重要走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相岭和邛崃山的大熊猫能彼此交流,有利于大相岭熊猫的复壮。但后来随着人类活动加剧,这片原本连通的熊猫栖息地被切得支离破碎。

首先是108国道的开通。它连接着荥经与汉源县城,很长时间里是一条流量巨大的交通要道。柏油路给山体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光是翻山就要两小时,冬季下雪后路面有暗冰,山上还会起雾,能见度很低,车轮胎都需要挂链条开,没挂就非常容易发生车祸”。一位附近的村民说,一有车祸就很快会堵车,少则几小时,多则三五天,形成一条鸣笛与车灯的汽车长龙,许多村民都会沿着这条长龙叫卖食物,颇有一种嘈杂的壮观。
更致命的是开矿和砍伐。泥巴山的山林成了经济增长的砝码,先是在1970年代建立了国有林场,开始大量伐木,后期又进驻了很多中小矿厂、水电站,直接在山体上开挖和建设,无休止地开发能源和花岗矿石。“那时候直接是推土机进去开路,然后人和机器就进去了,在山体上天天‘哒哒哒’地冲击。”附近的村民说。我们巡护的山体中,就不时布满了零碎的石块。
人类活动的侵扰,在荥经县的龙苍沟镇最为剧烈。这是大相岭山系往里的一处大山沟,处在“L”形夹角之内,是“雨城”雅安降雨量最多的地方,气候四季温润潮湿,森林植被更加茂密,也因之遭到了最惨痛的砍伐和开采。
“五六十年代就开始砍,砍的都是天然林。那时候国家要修铁路,很多树木就被砍了当成铁路上的枕木了,尤其是冷杉。”62岁的龙苍沟镇发展村村民黄建银回忆,当地森林里长满了一种类似苔藓的草,因质地柔软被称为“泡草”,“像走在地毯上一样”,后来也被开采,卖到港台等地供给当地人的鱼缸。还有不少水青冈(也称山毛榉)也被砍掉。这类木头很硬却又不失细腻,纹路漂亮,常用作木地板,“当时就能卖到上千元一立方米”。这些林子被成片地砍,如果新树还没长起来,就没有可砍的了。

四川雅安市荥经县龙苍沟镇常年云雾缭绕,黄建银就生长于此
“那时候为了生存没得办法。”黄建银说。山里还盛产一种八月竹,每年8月就漫山遍野地发笋,很多村民会上山打猎和采笋。这在上世纪80年代越发频繁。随着改革开放,有很多老板来此承包山林,受雇于这些老板的民工大量从周边县市拥来“打笋”,“一到季节就是成千上万人,漫山遍野都是人在打。林子基本就在那时候毁了”。
这种人类活动的侵扰,让整个四川在上世纪70年代后栖息地大面积退化,代价是野生大熊猫数量从1970年代第一次调查时的近2500只,断崖式地下降到1980年代末第二普查的约1100只。其中,依附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大相岭所在的荥经县一度是全省山区县经济发展榜首,大力发展占全县GDP约70%的石头、木头、水头“三头经济”。但在第二、三次普查中,大相岭山系的野生大熊猫数量分别只有20只、16只,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而这些数量极少的大熊猫,还可被分为三个更小的细分种群,最小的甚至不足三只。
“我小时候在海拔1400米都看见过熊猫,后面就越走越高、越走越远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有保护意识了,不会打扰它,但它还是一看到猎狗就爬上树躲避。”黄建银说,“大熊猫就是这样,一旦受到了惊吓,它可能就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第18期,阅读全文请移步杂志)

排版:初初 / 审核:雅婷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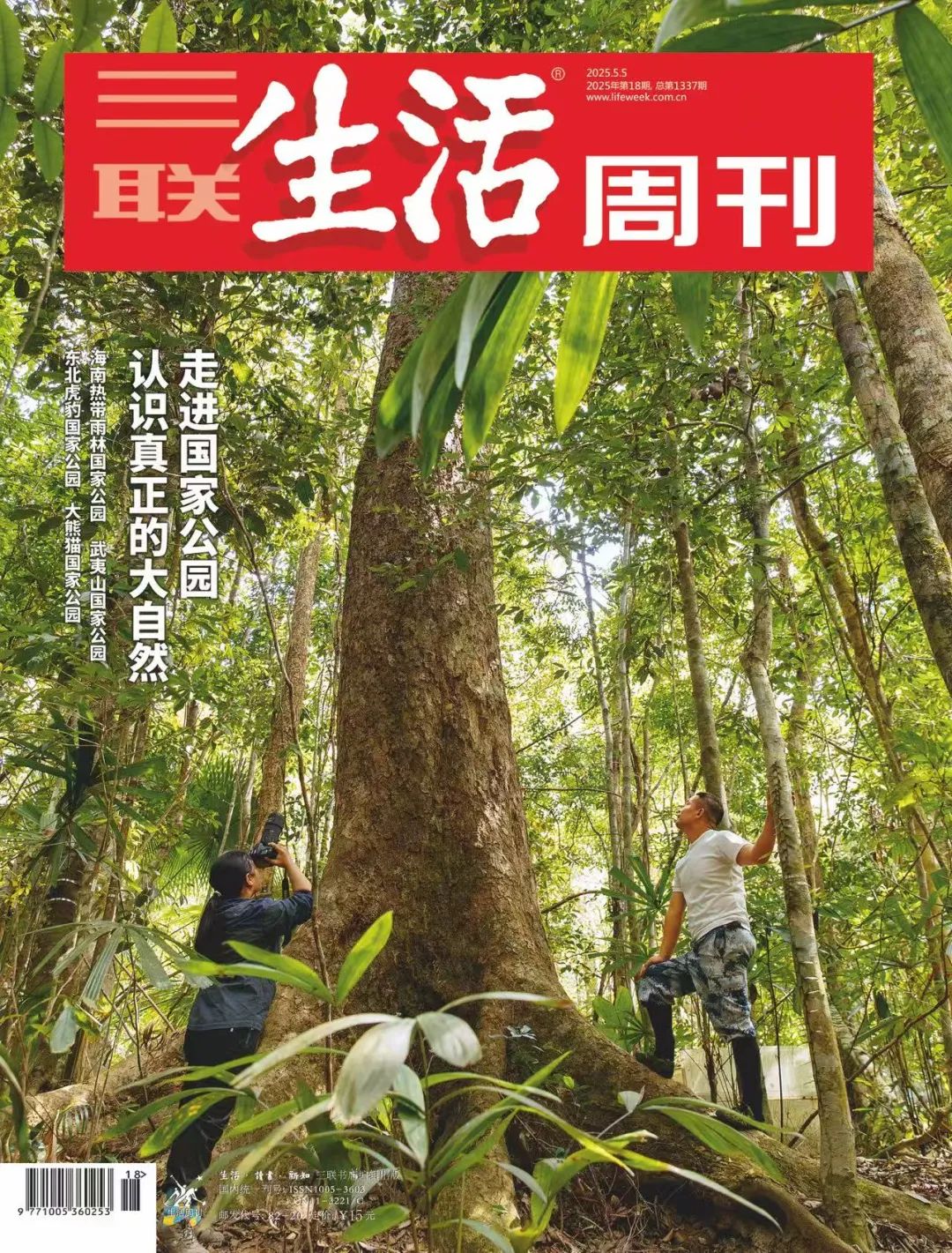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5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5975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