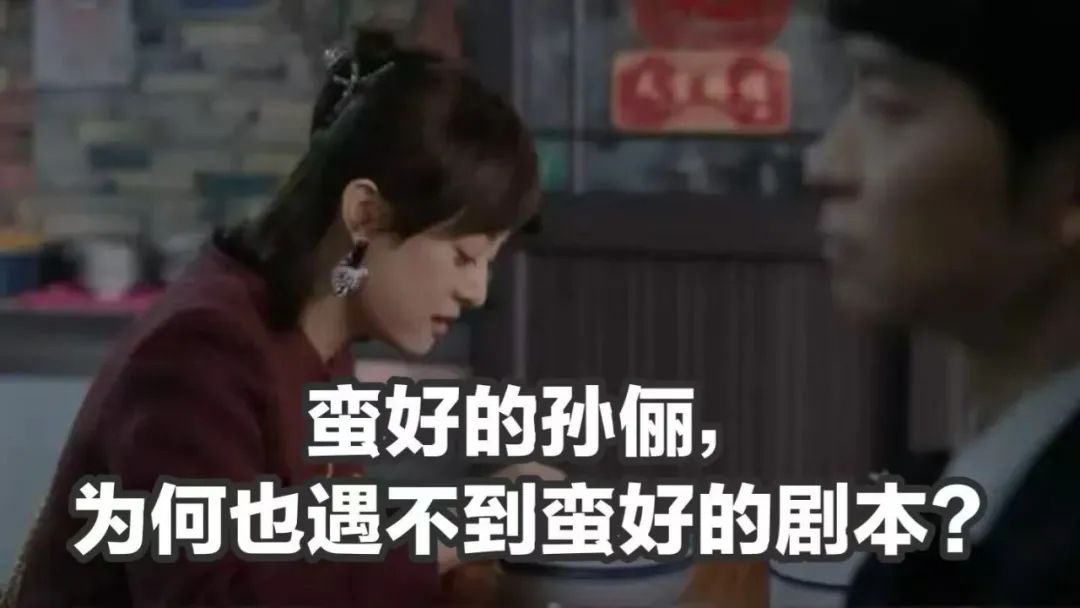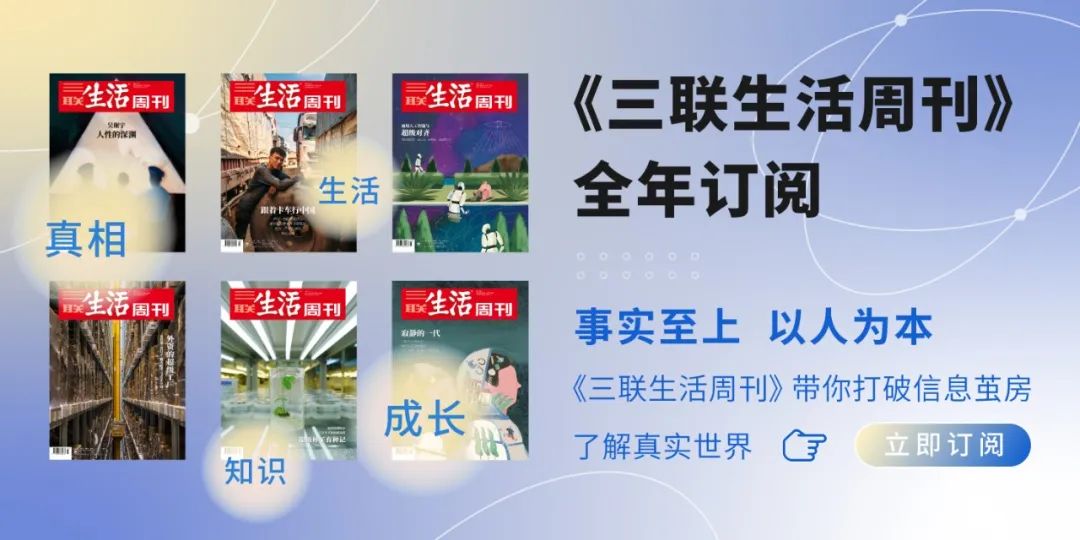一个美国婚纱商经历的关税风波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5-16·阅读时长29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每卖出一条裙子,亏250美元
自2月份以来,我们一直在支付不断增加的关税。作为进口商,关税100%由我们支付,而不是由中国的制造商承担。这是FOB(Free On Board,也即离岸价)的规定。也就是说,从货物抵达美国的那一刻起,海关就从我们的账户里把钱抽出去了。
我们旗下有12个子品牌,其中5个专注于婚纱,另外7个则涵盖了各式各样的礼裙——从晚礼服、新娘母亲穿的礼裙,到专为西班牙裔成年礼提供的礼裙,基本上是美国同行里品类最丰富的大品牌。我们在中国有40家合作工厂,其中13家专门生产婚纱,剩下的27家负责其他类型的礼服。我们的婚纱价格定位在美国市场的中档,这个价位恰好是销量最为可观的那一档。与中国的工厂合作,我们共同设计,随后由中国厂家生产,成品再运往美国。
2月1日,第一次加征10%,我们决定消化这笔账,付关税,继续给零售商出货。3月3日,第二次加征10%。我们再次扛下来了。结果到了4月2日,关税一口气涨了34%,还没来得及反应,短短六天后,关税又涨了50个点。这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真的撑不住了,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没想到,接下来还发生了更糟的事情。两天后,加征的关税一口气飙升到145%。婚纱和礼服本来就已经有16%的进口关税,算是美国商品里最高的一档,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又给中国加了7.5%的关税,现在加上今年新加的,税率已经高达168.5%。

与Mon Cheri合作的一家潮州工厂,存放着许多礼服裙成品(张雷 摄)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中国厂家进货的价格在250到300美元之间,然后卖给零售商的价格是700美元左右,最后在商场里的零售价能卖到1600到2000美元。可是现在,关税高达168.5%,那件进货价300美元的衣服,成本就变成了800多美元。每卖出一条裙子,我们大概就亏250美元。因为客户的订单都是关税上涨前四到六个月就下了的,是要交给新娘办婚礼用的,我们不能提价,也不能毁约,即使亏损也不得不出货。这事关我们客户的人生大事,也关乎我们在行业内的名誉。
1月,我们一个月出货接近1000万美元,到了3月数字减半。4月初,我们叫停了在中国的所有生产线。
我也在想办法把这个成本转出去一些。2、3月份的时候,我开始和已经下单的零售商商量分摊关税的事,最后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就是在零售价格上加上一项附加费,让消费者承担一部分关税成本,这样我们和零售商都能挽回一些损失。现在,我们在全行业推广这种做法,目的是让客户明明白白地知道关税对价格的影响。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多出来的附加费会大大降低我们的销量。如果你回顾过去10年的趋势,你会发现美国所有东西都涨价了,但婚纱的价格几乎没涨过。原因之一是,美国年轻人结婚的年龄推迟了,不再是20多岁,而是30多岁。这些人已经从家里独立出去,婚礼开销往往是自己负责,而不像过去,父母会帮忙出一部分。另一个原因是婚纱的意义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年轻人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把婚礼和情感深深绑定在一起。对他们来说,婚礼不过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婚纱也只是一件必须穿的“制服”。如果品牌婚纱的价格过高,消费者会选择更便宜的替代品,我们的市场份额就会丢掉。
第二个棘手的问题是,从我们支付关税,到将裙子交给新娘,中间有大约90天的等待期。换句话说,我们还不能马上把货款收回来,这样我们根本没办法保持正常的资金周转,除非接新的订单。这种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婚纱与礼服行业协会主席史蒂芬·朗(受访者 供图)
我也在和中国的生产厂家商讨,看看能否分担一些成本。许多厂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价格减免,像是10%的折扣,但这些几十美元的降价,与我们需要支付的几百美元关税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
在这一场关税的“海啸”中,我们批发商是站在第一排的,接下来这个浪会压到我们在美国的3000个零售商身上,然后再传给消费者。至今,我还没有看到消费者抢购或囤货的现象,大家似乎感知不到什么变化,因为零售商还有库存可以消耗。但我认为,很快,在未来的两到三个月里,美国货架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会被清空,消费者将真正感受到这场海啸的威力。
我们目前的服装库存大约价值1700万美元。试想一下,如果按目前的关税标准,我们需要向政府缴纳多少费用。交给政府的钱,已经超过我们支付给中国制造商的钱,这简直是不可理喻。
婚纱行业大多数都是中小型家族企业,每个企业的损失都非常惨重。我知道也有一些婚纱品牌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生产的,但这些都属于高端品牌,市场份额非常小,出货量和公司规模也都有限。4月19日,我们婚纱与礼服行业协会发起了联署,要求免除礼服关税,3000多家公司的代表都签了字,但政府对此没有任何回应。我们去找了所有愿意倾听的政客,但民主党由于没有实权,只能等待中期选举,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而共和党人则与特朗普保持一致。现在,所有人都在等待特朗普采取行动,直到情况恶化到一定程度,股市继续下跌,特朗普的支持率下降,然后他身边的党内人士才可能意识到,这种局面必须停止。
除了等待,我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特朗普像风一样反复无常,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我们公司有100多名员工和50多位销售人员,如今因为订单断崖式下滑,销售的奖金已经归零。眼下我们还能发工资,但最多也就撑六个月。这不是我们一家的困境,而是整个行业都在濒临崩溃。

2015年上海时装周Mon Cheri 品牌秀场(视觉中国|供图)
有人建议我转口,把婚纱拆成零部件运到第三国组装,以此绕过关税。我拒绝了。现在美国政府查得极严。我的律师刚告诉我一个案例,有人进口虾时从越南中转被查出来,判刑两年。法律规定,如果商品的主要价值来自中国,那原产国就必须标注为中国,任何伪装都可能被识破。
我也听说有些中国工厂在走低价申报的方法,比如把100美元的货品申报成20美元,从而帮买家少缴税。但这同样风险巨大。拜登在2024年10月签署了一项法律,规定如关税未缴清,无论是出口方还是收货方都要负责,收货人最高可判刑10年。据我了解,美国政府已经通过打击低价申报收了近4亿美元的罚款,甚至用上了人工智能来识别申报异常的货物。现在不是钻空子的时机。对我们这样的品牌来说,一次违规都可能是致命打击。失去生意是一回事,坐牢是另一回事。
中国工人手工精细、勤奋,难以替代
我早就预料到特朗普会上调对中国的关税,但没想到幅度会这么大。去年竞选期间,他确实放出话说要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但我和身边的人都以为那只是说说而已,不太可能真的兑现。我原本的判断是上涨20%到30%,就像他第一任期时候那样。那种程度的打击,我们还能通过压缩利润、向银行贷款勉强撑过去,熬到他任期结束。但我没想到,现实的冲击会严重到把公司推向破产的边缘。
我们90%以上的生产线都放在中国,最核心的考量就是成本控制。婚纱的成本构成里,最大的一块就是人工。我们生产的婚纱大多需要大量精细的手工操作,机器根本替代不了,工艺的复杂程度也直接决定了工时和成本。最典型的例子是珠绣。如果一条裙子不做珠绣,可能只需要20个小时完成;但一旦加上复杂的珠绣工艺,制作时间可能就要翻倍,甚至达到100个小时。如果你在美国雇一个熟练工,时薪大约是30美元,而在中国,只要5美元。
但这不仅仅是人工成本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在别的国家,你很难找到像中国这样大批量、经验丰富、手工精细的缝纫工人。坦白说,这些年来,与中国做生意的确定性确实在下降。一方面是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朗普政府把中国视为对手,而中方的反应也非常强硬;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持续上升。
其实,早在八九年前,就有一些做欧洲市场的美国婚纱品牌开始转移生产线,比如搬去缅甸。因为从2012年开始,欧盟对缅甸商品实施免关税政策,在那里设厂可以省下将近12%的税款。这些变化促使一部分企业早早布局,但对像我们这样深扎中国多年的品牌来说,转身并不容易。

Mon Cheri位于新泽西州兰伯特维尔的婚纱陈列厅(视觉中国 供图)
其实,我也不是没考虑过把生产线迁出去。那几年,我去过缅甸、印度、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和越南做考察,但每到一个地方,总觉得时机还不成熟。这些地方普遍缺的不只是工厂和设备,还有好的工匠。一针一线的手艺,不是十天半个月就能学会的。尤其是做蕾丝和珠绣,那是真正考验功夫的活儿。哪怕只是照着纸样钉珠,不同的工人做出来,珠子的角度、花瓣的走向都会略有偏差,成品出来,效果天差地别。要做出细致、稳定的品质,不光靠培训,还要靠经验的积累,靠时间的打磨。
在这一点上,中国供应链的确定性和成熟度,是其他国家很难替代的。中国工人不仅手艺好,还特别勤奋、可靠,出货也快。东南亚有些地方的问题就在于交期不稳,这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婚纱行业讲究准时,每一条裙子背后都是一场婚礼,是不能耽误的。我是犹太人,在美国商人里,我算是拼命工作的那种,一周七天都在忙。但我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身上,看到了一种和我们文化相近的敬业精神,那种愿意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劲头。
更重要的是,中国几十年来形成的原材料供应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不光是丝绸,连底布、三醋酸面料、蕾丝、珠子⋯⋯很多材料在其他国家根本找不到现成的替代品。这不是短时间能复制的。
所以,我最终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我们现在还有40家工厂设在中国,另外在越南和缅甸各有两家工厂。最大的一个厂有1000名工人,已经是相当于中国一线代工厂的规模了。这些海外工厂基本都是中国合作方出资、派人管理,能承接部分礼服生产,但真正中高端的婚纱,还是得放在中国做。
特朗普政府一直在鼓励制造业“回流”,希望我们把生产线搬回美国。我觉得这根本不现实。2019年他第一次加征25%关税时,我作为行业协会主席参加了听证会。在会上我就说得很直白:“我们没办法把婚纱搬回美国做。”我问在场的一位参议员:“你有孩子吗?”他说有。我又问:“他们上过缝纫学校吗?”他说没有。“那你身边有谁的孩子在学缝纫吗?”答案还是没有。我说:“这就是问题所在。美国人不愿意进工厂,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进工厂。你告诉我,我去哪儿找工人?”
婚纱制造不是一般的流水线活儿,它需要技艺和耐心。而服装制造业,早在“二战”结束那段时间就已经是最早一批被外移的行业之一。美国早已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性的基础。

2020年,波士顿纽伯里街一家婚纱店的老板正在店里忙碌
有人说,也许再过几年,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美国人也会愿意去做缝纫工。但问题是,建厂不是动动念头的事,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时间。万一三年半后,民主党重新执政,或者拿下国会的任何一院,关税政策就可能被推翻,一切回到从前。那时,我辛辛苦苦砸进去的几亿美元,岂不是打了水漂?
作为一个商人,我不会下这种赌注。更何况,就拿我所在的新泽西来说,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5美元。在这样的成本下,婚纱的价格将高得离谱,根本不是普通消费者买得起的。
婚纱工厂1980年代就在美国生存不了了
我第一次和中国人做生意,还是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台湾。那时我还没有创办Mon Cheri,而是在一家美国婚纱公司工作。那个年代,美国市场上的婚纱几乎都是本土制造的,珠饰靠工人一颗颗用胶枪粘上去。
1983年,在美国的一场展会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台湾生产的婚纱。那是由两家率先将供应链外包到海外的美国公司带来的样品。我一眼就被吸引住了——这些婚纱的售价和我们自己做的差不多,但珠饰精致得多,全是手工缝制的,立体感十足,和我们用胶枪粘出的平面效果完全不同。
这类珠饰不仅更美观,还让婚纱看起来更合身、更有结构感。当时正值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人普遍发福,市场对“显瘦”的需求在变高。这些手工珠饰巧妙地把视觉焦点集中在身体中轴线上,而不是外缘,自然显得更苗条、更挺拔,完美贴合当时的审美潮流。
展会回来后,我立刻对老板说,我们必须把供应链搬到海外。他不同意,说我们在宾夕法尼亚有那么多工厂,工会不会答应。但我态度很坚决,还和他吵了一架。我说,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过去的模式,很快就会失去市场。最后他松了口,让我去中国台湾考察。
我在中国台湾找到几家工厂,订了一打婚纱运回美国。当时老板的女儿也是公司里的设计师。她看到这些婚纱的第一反应是转身对家人说了一句话:“我们完了。”那一刻我们都明白:如果还拿美国制造的婚纱去跟这样的产品竞争,我们撑不了几年,结局只会是出局。

与Mon Cheri合作的一家潮州工厂,工人们在制作销往美国的婚纱和礼服(张雷 摄)
那时我决定离开原来的公司,开始自己创业。我不再涉足生产环节,而是专注于从海外引进服装。我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美国人,但也算是走在前列的那一批。当时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是40比1,雇一个中国台湾的工人每天的工资不过6到10美元,大概只有美国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而且中国台湾的设计教育体系很完善,学校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设计师和技术人员,产品既有成本优势,也有质量保障。
不过,中国台湾的发展速度很快,这些婚纱工厂在当地并没有待太久。随着美资大量涌入,其产业结构迅速转型,高科技取代了劳动密集型制造,生活水平提高,人工也变得昂贵。于是,许多台商开始向中国大陆转移产能,在东南沿海设厂、投资,并培训工人。那个转移过程非常顺畅——语言文化相通,加上熟悉的合作关系,我的生产线也随着中国台湾的合作伙伴迁到了大陆。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到潮州时,那里的基础设施还很落后,连路灯都很少见,有辆自行车就算是富裕人家。但让我惊艳的,是潮州深厚的手工艺传统,尤其是潮绣。当地工人原本就有扎实的珠绣基础,只需稍作培训,就能完美呈现我们的设计需求。而且,他们对订单的态度非常积极。那次在一家工厂里,我看到一个母亲正在缝纫,缝纫机底下的篮子里,躺着她襁褓中的婴儿。我心里一紧,转头对工厂经理说:“这太让人难过了,我是不是在压榨他们?”对方摇头说:“不,你搞错了。如果没有这些订单,她的孩子才恐怕要挨饿。”
我始终心怀感激——我们站在产业链的上游,靠着中国稳定而强大的供应链赚了很多钱。中国承担了劳动力、环境等多方面的投入,支撑起了这套体系。特朗普只看到一件事,就是把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但他忽略了,我们在中国投入的每一分钱,都在带动这些工厂成长,反过来帮了我们大忙。这是产业协作与全球分工的成果。
当然,做生意这么多年,我们在中国也不是没有碰过壁。在关税战爆发之前,最大的挑战来自假货横行。大概是在2010年前后,我们陆续接到客户投诉,说在网上买到的礼裙质量很差,一查才发现是假货。有一些商家直接盗用我们的产品图片,搭建看起来像官方的网站,把原本标价2000美元的婚纱,用99、129、399美元的价格出售。

2012年,我们成立了美国婚纱与礼服行业协会,最初就是为了集中力量应对假冒问题。我们追溯造假的源头,打了12场官司,最后不仅拿到了赔偿,还关闭了造假网站,并从互联网上删除了盗图。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也是一场胜利。现在,假货问题已经明显减少,造假者知道我们会追责到底,不敢轻举妄动。
疫情也是一次不小的冲击,但美国政府推出了PPP(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即工资保障计划),我们得以以极低的利率获得贷款,保证员工薪资的发放,总体上还算平稳地度过了那一段时间。
可眼下的局势完全不同。在关税面前,我没有任何法律或政策可以依靠,也没有渠道向上反映。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开始怀疑,把大部分产能留在中国是不是一个错误。我开始想,也许我早该更谨慎些,把鸡蛋分散到不同的篮子里。
这些年,我们与中国工厂是彼此成就的关系。我飞去中国的次数超过65次,几乎年年都去。潮州、中山、厦门——我亲眼看着两层的小楼房,一点点被高楼取代,见证了中国令人震撼的发展速度。
也正因为看得够多,我猜测中国大陆终究会走上和中国台湾一样的路——成本上升,产业升级。前几年我在中国东南沿海考察时就发现,一些合作工厂已经开始招不到年轻工人,生产线上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人,也快退休了。年轻人不再愿意进厂,父母们也更希望孩子从事脑力劳动。中国东部的劳动力开始紧张,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说到底,我们终将撤出,只是时间的问题。但问题是,这种调整需要时间。而在眼下这轮猛烈的关税打击下,我真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撑到完成转移的那一天。

这几个月,中美关税层层加码,我们这些做进口生意的人,就像夹在两头大象之间,喘不过气来。我想,双方如果谈判把关税定在25%,行业还能承受,生意还能继续。毕竟,真正受益的,是两国的普通百姓。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第20期,实习生余雯彤对本文亦有贡献)

排版:初初 / 审核:雅婷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5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5977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