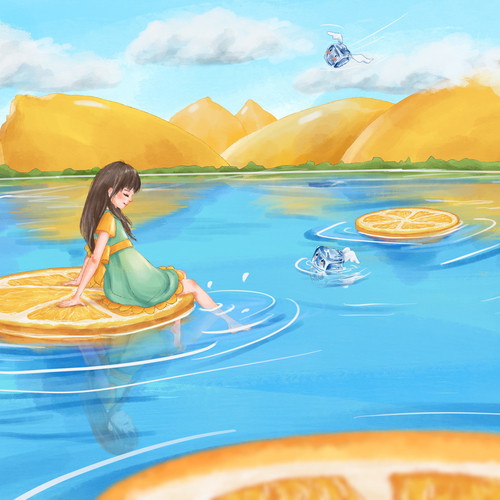《末代帝王君》第六章 诤臣直谏
作者:余味
2018-03-30·阅读时长19分钟
第六章 诤臣直谏
因为身体有伤我的学业便被暂停了半个月,待到半个月之后我的伤基本已经痊愈,翁同龢才来重新给我上课。我将自己在风月楼遇到如烟及其悲惨遭遇之事一并告诉了翁同龢,当然如烟诅咒大清覆灭的话我丝毫未予提及。罢了我说道:“朕一定要为如烟一家人沉冤昭雪,若不如此,则民心尽失矣!”翁同龢说道:“皇上岂能轻信风尘女子的一面之词?此事必须经过刑部调查才可处置,然而皇上如今还未亲政,因而调查之事也无从谈起。一切还是等皇上亲政后再说吧!”我知道皇太后对于朝廷有着绝对的掌控,刑部的大小官员一律听命于她,我还未亲政自然不便过问朝堂之事。本来还想去向皇太后求情,但一想到我上次便是因为去风月楼而遭受责打,倘使再让皇太后知道我是为妓女翻案定会惹得她大怒,所以我只得隐忍着暂不处理此事。虽然我心有不甘,但目前我的确无可奈何,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早日亲政以处理家国大事。身为当朝天子却不能为百姓主持公道,我内心自是颇为不满,正是因此我也无心听课,翁同龢倒也体谅我而不去计较。
说来也巧,今日朝堂将散之时太常寺卿杨酬恩大声说道:“启禀皇上,微臣有要事启奏。”我扫了皇太后一眼,见她没有阻止的意味便顺水推舟地说道:“哦,杨爱卿有何事要奏?”杨酬恩答道:“启禀皇上,昔日皇上年幼才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如今皇上已经年满十六,具备了处理朝廷政事的能力。因而微臣建议皇太后及时撤帘归政,以将权力完全归还皇上,以使皇上名正言顺的坐镇朝堂处理国家政事。”我听了大感欣喜,这正是我日夜企盼之事,然而皇太后却面露不悦之色,她举着自己的拐杖戳了戳我,示意我让杨酬恩停止说话,我却对此未加理会以便杨酬恩继续说下去。只见杨酬恩继续说道:“自古以来皇位是授予天子而不是授予皇太后,皇帝才是江山的正统,是社稷的根基,因而皇上当朝理政也是自然之事。以前皇上幼小不得已才使用垂帘听政之法,如今皇上已近成年,完全可以自立,皇太后已为我大清操持了近三十年,此时也应该坐立后宫颐养天年。垂帘听政本就不是我朝的风俗,当时不得已才为之,如今断没有垂帘听政的必要了。况且我朝高宗皇帝曾经明确禁止后宫干政,祖先的遗训后世子孙不得不遵从,因而皇太后应该及时撤帘归政于皇上,如此上承天意下守祖训。”
我虽然对撤帘归政之事极为欢喜,但最终的决定权在皇太后手里,因而我不敢贸然发表意见,于是我转头向帘子后面的皇太后问道:“此事关系重大,还请皇爸爸示意。”皇太后没有发表意见,转而说道:“诸位大臣都是什么想法?大家都说来听听。”这时荣禄赶紧乘机说道:“臣以为现在谈及皇上亲政之事尚且过早,眼下大清事事都离不开皇太后,倘若皇太后此时对朝堂之事撒手不管,那么大清必然乱成一团,到时朝局自然难以收拾。因而臣坚持皇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如此方能保我大清安宁太平。”这时礼部右侍郎徐桐附和道:“老臣以为荣大人所言甚是,当今我大清不可一日无皇太后,撤帘归政实属荒唐。”杨酬恩指着徐桐骂道:“你这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也敢在这里胡说!自古以来都是天子治理国家,如今皇上已到了亲政的年龄,撤帘归政是必成之事,更是人心所向。你怎敢公然违背天地人心说出这样荒唐的话来?”徐桐反驳道:“皇上究竟年幼,从未处理过政务,处事经验显然不足,而与之相比皇太后处理朝堂政务早已得心应手。我等为人臣子,自当为江山社稷思虑,怎么能弃皇太后而不顾呢?”
杨酬恩怒斥道:“不让皇上亲政,皇上就永无处理政事的经验,你以为这处事的经验是与生俱来的么?当年康熙爷十四岁亲政,还不是一点一滴积累治国经验,这才有我大清的康熙盛世。今日皇上已经十六岁,如何就不能亲政?”徐桐说道:“康熙爷是康熙爷,皇上是皇上。今日大清的情况不同于往日,你也就不要拿来做对比,当年康熙爷的身边可没有皇太后这样的人等。”杨酬恩驳斥道:“怎么没有?当年孝庄文太后圣明有谋,难道比不上今日的皇太后吗?”徐桐没有回答,转而说道:“以臣愚见,应该听听满朝官员的意见再做定夺。”皇太后点头说道:“好,我正想听听大伙的意见。这样吧,赞同撤帘归政的大臣站在东侧,赞同继续垂帘听政的大臣站在西侧。”皇太后刚一说完所有的大臣都跑到了西侧,东侧只站着杨酬恩一人,我对此大感失望。与我相反,皇太后甚是得意,只见她说道:“老实跟你们说吧,其实我也不想垂帘听政。”“那就请皇太后即刻撤帘归政,如此也遂了您的心愿。”杨酬恩插嘴如此说道。
皇太后狠狠瞪了他一眼,所幸隔着帘子杨酬恩应该看不见,只见皇太后接着说道:“可是纵然我有一万个不情愿,诸位朝臣执意让我垂帘听政,我也不得不如此,以免违背民意伤了大家的心。”荣禄又接着说道:“皇太后圣明。朝廷上下都希望您主持朝政,只有那些不识时务的小人才希望您撤帘归政,您又何苦与这样的蝼蚁之辈计较呢?”皇太后接着说道:“撤帘归政之事就暂且搁置,等以后时机成熟再说。”杨酬恩喊道:“撤帘归政之事决不能搁置,皇太后要是今日不答应,臣以后每日上朝都要参奏此事。”皇太后没有理会,而是说道:“今日早朝就上到这里,大伙都散了吧。”
下朝后群臣全都散去,皇太后问我道:“皇帝,你怎么看撤帘归政之事?”我知道皇太后有着强烈的权利控,今日在朝堂上便可看出,所以我只得违心说道:“儿臣也是赞同列位臣工的意见。”皇太后又问道:“那你怎么看杨酬恩这个人?”我知道皇太后此时已经对杨酬恩极为不满,便顺着说道:“儿臣以为杨酬恩妄提建议,实属不该,冒犯皇爸爸更是缺乏人臣之礼。”皇太后接着说道:“对于这样的人必须严惩不贷,否则以后岂不是人人都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依我看,应该把杨酬恩砍了脑袋。”我赶忙转口说道:“可是杨酬恩毕竟是三朝元老,当年杨酬恩和他父亲围剿太平军出力甚多,为大清立下了不小的功劳,这样处罚功臣未免说不过去。再说了,他今日所谈的撤帘归政之事是为了大清社稷着想,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这说明他忠心可嘉,如此把他杀了未免给人落下话柄。”皇太后气愤地说道:“这么说你就不打算追究他冒犯我的责任?”我又补充道:“依儿臣看,就对他罚俸半年吧。”皇太后摇头说道:“不行,这处罚太轻了。”我又说道:“那就把他官降一级,再罚俸半年,这总行了吧?杨酬恩毕竟是有功于大清的老臣,处罚太重了未免有失公允。”皇太后极不情愿地说道:“今日我就听你一次,倘若他再敢对我无礼,下次定要砍了他的脑袋。”皇太后说罢扬长而去。
我知道皇太后向来说到做到,对于仇敌她更是毫不手软,于是我立即着人悄悄去杨酬恩的府邸送信,告诫他以后不要再提撤帘归政之事。回到养心殿后,我将今日杨酬恩上奏之事说与了清月,她兴奋地说道:“这么说皇上有望亲政掌权了,奴婢真为您感到高兴。”我说道:“可是皇太后丝毫没有归政的意思,朝中的大臣除了杨酬恩外也都支持皇太后。唉!朕的亲政之路并不平坦。”清月见我面露忧愁,便说道:“皇上不必泄气,奴婢打心眼里希望您早日亲政,而且奴婢深信这样的时刻不远了,皇上不妨再等等看。”我听了顿感欣慰,说道:“有你支持朕心里宽慰多了。”清月笑了笑说道:“皇上要是亲政,一定要亲民恤民,做一个宽厚仁和的圣明君主,如此奴婢就代天下百姓感谢皇上。”我说道:“圣明君主倒不敢求,但朕绝不会做桀纣那样荒淫无道的昏君。”清月又道:“这是自然,在奴婢看来皇上日后必是大有为的君主,能伺候这样的主子奴婢深感荣幸。”我说道:“宫里的奴仆大都喜欢曲意逢迎,怎么如今连你也学会了这套?”清月一脸真挚地说道:“奴婢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您要是不喜欢奴婢以后就不说了。”随后她又补充道:“要是皇上喜欢听批判讽刺的话,奴婢也可以日日说与皇上听。”我知道她这是玩笑之语,倒也没有细加理会,不过一笑而置之。
第二日授课时我见到了翁同龢,便质问他道:“昨日朝堂上翁师傅没有表态支持杨酬恩的提议,难道翁师傅不想让朕早日亲政吗?”翁同龢大概已经料到我会如此发问,因而没有什么惊诧的表情,只见他说道:“皇上还是先诵读功课,亲政之事以后再说。”我不满地说道:“倘若不能够亲政,那么功课做得再好又有何用?圣贤的文章终究是纸上的东西,不亲自体会一番又怎能理解?朕现在是空有皇帝之名,却无皇帝之实,如此的境遇又怎么能够把书读进去?”翁同龢叹了口气,说道:“既然如此,那老臣不妨直说了。”我搬了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来说,他却仍旧站着说道:“自从辛酉政变至今,皇太后已经掌权达二十六年,现在朝廷里哪个重臣不是听命于皇太后?六部尚书哪个不是皇太后一手提拔的?六部侍郎哪个不是皇太后栽培出来的?各省的总督与巡抚又有哪个不是皇太后的亲信?至于荣禄徐桐等辈更是唯皇太后马首是瞻,自是不用多说。”
翁同龢捋了捋胡须继续说道:“这种局面不是一日两日就形成的,自然也绝非朝夕之间可以解决。朝廷上下人人皆知皇太后并无撤帘归政之意。如今皇上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朝廷中又没有实权派的大臣倾心支持,地方上又没有封疆大吏鼎力相助,又怎能迫使皇太后归政呢?”翁同龢顿了顿又道:“杨酬恩固然全力支持皇上亲政,可他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常寺卿,所谓人微言贱,朝中的列位臣工又怎会在意他的提议?因而皇上此时不宜积极附和,以免皇太后窥探到你想要亲政的心思。”我说道:“朕一日不表露想要亲政的心思,皇太后便一日不会归政,难道朕一定要等到皇太后魂游仙山时才能握权理政吗?”翁同龢说道:“皇上绝不能在此刻表露出亲政的愿望,而是要等到皇太后亲自提出撤帘归政时再装作勉为其难地接受,如此才能不引发皇太后的猜忌。这固然还需要等不少时日,但皇上切记欲速则不达。倘若此时皇上赞同杨酬恩的提议,便有夺权逼宫的嫌疑,势必会引发皇太后的全力反击。试问皇上,此时与皇太后公然决裂你有几成胜算?显而易见,这无异于以卵击石。为求自保和长存,皇上还是要学会忍耐。”
我失望地说道:“可是,如果皇太后一直不提出撤帘归政的主张呢?那朕岂不是要一直等下去?”翁同龢微微一笑,说道:“这个皇上不必多虑。等到皇上举行成亲大典后皇太后便不得不归政。举行成亲大典是一个人完全成年独立的标志,纵使皇太后百般恋权,待到那时皇太后就再也没有不归政的理由了。退一步讲,倘若那时皇太后仍不归政,老臣也要联合朝臣请她归政于皇上。”我听后顿时看到了希望,忙说道:“翁师傅,原来你早就想好了一切,朕真是错怪你了。”翁同龢笑着说道:“老臣昨日没有没有站出来支持杨酬恩的提议,一是为保皇上,二是为保自己。不过皇上放心,老臣的心始终向着皇上,只要时机成熟,老臣一定会为皇上争取亲政之事,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我听了大为感动,忙说道:“翁师傅待朕如此赤诚,请受朕一拜。”翁同龢赶忙阻止道:“使不得,皇上,万万使不得。”我说道:“咱们之前说好了,在朝堂上朕是皇帝你是大臣,在毓庆宫中你是师傅朕是学生,师傅受学生一拜有何不可?”我坚持了行完了一礼,翁同龢将我扶起,含泪说道:“老臣当年教辅同治帝时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的礼遇,今日受皇上行此大礼,老臣虽死无憾矣!”
经过翁同龢的一番劝诫,我感到茅塞顿开,既然翁同龢对此早有谋划,我就不必过分忧虑,此刻倒也不宜操之过急。因为心情舒畅,我今日读书也比往日更为用功,翁同龢看了颇为欣喜。晨读过后吃过早饭我便赶来上朝,皇太后见我气色不错便问道:“看你今日颇为欣喜,是不是有什么高兴的事?”我答道:“儿臣见到皇爸爸天颜自然感到心悦。”皇太后自然不信,但也是笑着不语而没有说什么。如同昨日一样,朝堂将散之时杨酬恩又启奏道:“启禀皇上,臣还要上奏祈求皇太后即日撤帘归政,好让皇上行理政之责。”皇太后的脸瞬间铁青了下来,冷峻白煞的面庞更甚于昨日。我在心底暗想:“杨酬恩,你可真够倔强!昨日秘密差人告诫你不要再上奏此事,没想到你今日又来上奏,真是让我何以言说?”老实讲,我是打心眼里赞赏杨酬恩身上的这种忠贞与坚毅,敢于不畏皇太后的淫威而直言上谏,当朝可能只有他一人能做到如此。但我此时深知现在不是提及亲政之事的绝佳时机,让他说下去只会惹恼皇太后而徒受处罚,于是我制止道:“杨爱卿所说之事昨日已经解决,因而就不用再说了。”
我本以为杨酬恩会因此而止住了口,哪成想他又开口说道:“皇上,昨日朝臣只是表明各自的态度而已,此事并未得到解决。”我抢着说道:“朕也是顺应列位臣工的心,愿意让皇太后继续垂帘听政,此事勿复再言。”我本想着给王晋田使眼色让他喊退朝,好结束这一切,没想到杨酬恩立即接口说道:“皇上,垂帘听政是当年不得已而为之,如今皇上已经具备了处理朝政的能力,因而断没有再继续垂帘听政的理由了。况且家国大事自古都是男儿处置,怎么能让妇人干政呢?”杨酬恩话一出口就引得皇太后拍了桌子,但他依旧神色不改地说道:“臣希望皇太后为江山社稷着想,早日让皇上亲政。”“够了。”皇太后大声斥责道,此时她的眼睛发红脸色铁青,显然已经十分震怒,只见她大声怒斥道:“杨酬恩,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公然在朝堂上放口乱言,谁给了你这么大的胆子?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太常寺卿而已,只管些管理宗族祭祀之事就好,什么时候轮到你插手国家政事了?你一个区区三品文官,留你上朝不过是充个人数,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朝廷栋梁了,竟敢公然在朝堂上如此撒野!”
杨酬恩脸上毫无惧色,答道:“回皇太后,臣不过是尽人臣之本分,做敢于直谏之臣。当年唐太宗善于听取魏征的意见,因而才有贞观之治,故而臣恳请皇太后效法唐太宗善于听取谏言。宋人范仲淹曾经说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臣虽不及范仲淹的才华,倒也颇有一腔热血和满身忠心,臣愿意效法魏征和范仲淹做一个敢于直言的诤臣。”皇太后骂道:“我呸!就你个无名小卒还想和魏征范仲淹相提并论,真是会给自个儿脸上贴金,还跑来给皇帝提建议,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你配吗?魏征当年给唐太宗提建议,不过是说些治国修身之事,他有劝唐太宗撤帘归政么?你这样肆无忌惮地狂言,倘若生在当时唐太宗也定要把你剁成肉酱!真是岂有此理!”杨酬恩说道:“统治江山的人自然该有博大的胸襟和宽广的心境,如此国家才可大治,反之国家必然衰败。皇太后应该容臣继续讲下去,而不应该讲出如此鄙陋的话来威吓臣。皇太后要是还不还政于皇上,恐怕会让人以为你权力欲望太重,这可不是圣明的统治者所为。”
皇太后骂道:“呸!权利欲望重又怎样?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为了权力杀害了自己的亲哥哥李建成和亲弟弟李元吉,最后逼得自己的父亲李渊退位,然后他才当上了皇上,这才有了贞观之治。难道唐太宗不是圣明的统治者么?唐太宗可以,我也一定可以。”杨酬恩说道:“可唐太宗终究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男子,岂是一个寻常妇人可比?”皇太后大声拍了桌子,骂道:“狗东西,你说谁是寻常妇人?”杨酬自知失言,便避开此话绕回正题说道:“臣觉得皇上已近成年,皇太后就应该及早归政于皇上,不要再行垂帘听政之举,毕竟这不合祖宗礼法。”皇太后继续骂道:“闭上你的狗嘴,祖宗的礼法岂是你一个太常寺卿说了算的?杨酬恩,你今天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跑到朝堂上来撒野,信不信我随时可以解了你的官职要了你的狗命?”
杨酬恩依旧面不改色,答道:“要杀要剐臣愿意听凭处置,只是我们杨家世受国恩,微臣父子两代深受先帝恩惠,愿秉承先帝遗志中兴大清,遵从先帝遗训不使妇人干政,以尽为臣之责。”皇太后怒道:“放肆,大胆的杨酬恩,你真把朝堂当你家了,敢在这胡言乱语。哼!既然你如此感念先帝,不如随先帝而去吧!来人,把这个口出狂言的家伙…”“慢着。”杨酬恩打断皇太后说道:“臣今日虽死不足惜,但是要皇上亲自下旨处死才可,妇人无权干预政事。”皇太后脸色煞白地说道:“你,你,好,我今日就让你死得心服口服,死得心服口服。皇帝。”皇太后愤怒地看着我,显然是希望我下令将杨酬恩处死,我小声对皇太后说道:“皇爸爸,杨酬恩虽然今日无礼,但念在他父子二人昔日对朝廷有功的份上就饶了他吧!”皇太后拍着桌子喊道:“绝不可能,这样目无法纪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必须杀一儆百,绝不能有丝毫手软。”
我却还在踌躇,因为我真的不想置杨酬恩于死地。见我不发话皇太后拿眼睛瞪着我,是希望我立刻将杨酬恩赐死,我却希望能够救他一命,便对皇太后说道:“皇爸爸,不如把杨酬恩打四十大板然后发配新疆充军,朝廷将其革职并且永不叙用。”皇太后咬着牙瞪了我一眼,那神情极为可怕,只见她说道:“不行,今日不杀杨酬恩,你以后就别叫我皇爸爸了,我就权当没你这个儿子!”皇太后的眼神变得愈加犀利,额角的青筋暴起,脸上的怒色也愈发加重,她咬着牙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如此可怕的表情我是既熟悉又陌生,以前也见过她发脾气时扭曲的表情,可是像这样凶神恶煞的表情我却是第一次见到。然而我还是想保全杨酬恩,可是面对这样可怕的皇太后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言语。皇太后怒目视我,见我不言语,就索性大拍一声桌子,高声咆哮道:“皇帝!”我着实吓坏了,不由得真真切切地打了一个寒颤。不得已,我只好违心地说道:“把杨酬恩拉出去斩了。”
话一说完,杨酬恩伏地嚎啕大哭,上来两个侍卫就要将他拉走,他却趴着不肯起来,侍卫只好将他往外拖,但他又挣扎着和侍卫打了起来,皇太后见此喊道:“大胆!你想造反么?”此时门外的侍卫们听到声响早已进来将杨酬恩团团围住。杨酬恩没有抵抗也没有屈从,而是大声说道:“皇上,臣不怪您,臣知道您也是身不由己。哼!叶赫那拉氏,你不过是先帝的一个卑微遗妾而已,到底不是大清门进来的正经主子,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朝堂之上?你执政二十六年,大清屈辱了二十六年。好好的一个大清被你搞地乌烟瘴气!你如此荼毒大清,将来必然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皇太后当年入宫时不过是咸丰帝的懿贵人,按照大清惯例只有皇后在成亲之时才可以从皇宫的正门大清门而过,其余的妃嫔只能从侧门而过。皇太后虽然如今身居高位,但是没能从大清门而过也是她无法改变的事实,对此她一直心怀愤恨。此外,在皇太后的统治下大清国向西洋诸国割地赔款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也确是皇太后的屈辱。如今杨酬恩将这两件事一同提起无异于是打了皇太后一记响亮的巴掌。
皇太后的怒气更甚,愤恨地说道:“今日不杀你难平我心中的怨恨,来人啊!快将杨酬恩这个逆贼拉出去砍了!”众侍卫压着杨酬恩准备下去,皇太后一甩手又喊道:“慢着。”众侍卫立即止住了脚步,我抱着最大的幻想以为皇太后要留杨酬恩一条性命,可是皇太后却凶神恶煞地说道:“不要砍他了,改判他凌迟,活剐三千六百刀,要一刀一刀割死他,绝不能让他死得痛快。”杨酬恩骂道:“慈禧刁妇,你纵使杀了我也改变不了我的心。我至死还是拥护皇上,我们全家老少都拥护皇上。”皇太后愤恨地说道:“那我就杀光你们全家。”随后转而对众侍卫说道:“今日杀了杨酬恩,然后再抄了他家,明日午时将他全家老少一并杀了。”众侍卫领命而去,杨酬恩被带下去时嘴里仍旧不停地骂着。
早朝就这样不欢而散,朝中大臣皆是人心惶惶,我知道此事过后大概再也没有人敢来提撤帘归政之事了吧!唉!杨酬恩也是一个有血性的忠臣,可怜竟这样无端丧命,我不由得替他惋惜。更可惜的是杨酬恩全家老少都得陪他丧命,我真是痛心至极!更让我难以心安的是下令杀死杨酬恩的人竟然是我——虽然我不大情愿,但也无可奈何。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杨酬恩直言上谏的目的是让我亲政,而我却下令杀死了他,我没有想到自己竟是这般凶残的刽子手,我的心中实在难受不已。恰恰是因为没有亲政掌权,所以连诛杀大臣这样的事情我也做不了主,只能违心地顺着皇太后的意思而行,我痛恨皇太后的贪婪恋权,我痛恨朝中大臣的趋炎附势,我痛恨自己的软弱无能!不,我一定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弥补这些。我发誓自己一定要亲政掌权,绝不能做让皇太后任意摆布的玩偶,杨酬恩一家的血不能白流。
回到养心殿之后我立马吩咐王晋田道:“去把大理寺卿朱经致秘密请来,一路上仔细点,不要让别人发觉。”王晋田应声而去。朱经致是我的伴读朱维国的父亲,他一向以刚正不阿著称,对我一直忠心不二,是我非常信赖的大臣。此次杨酬恩抄家及对其家人行刑的直接负责官员就是朱经致,故而我特意请他前来。朱经致穿着太监的服饰赶来,还没有来得及请安我便屏退了左右,然后开门见山地对他说道:“朕有一要紧事,非朱爱卿不能为之,还望爱卿成全。”朱经致看了我一眼,压低了声音说道:“皇上所说可是杨酬恩之事?”我点了点头,他继续说道:“其实微臣也甚为钦佩杨大人的忠贞爱国之心,对于杨大人要遭此难深表痛惜,但皇上以帝王之尊尚不能保全杨酬恩,微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大理寺卿,自然对此也无力回天。”我说道:“朕知道你对此无可奈何,朕也无法改变杨酬恩凌迟处死全家株连的结局,朕只是希望你在监督行刑时能够网开一面。”朱经致问道:“皇上的意思是?”我说道:“皇太后下令将杨家男女老少都一概诛尽,朕希望你能够暗中做些手脚,给杨家留一个男丁,不要让杨酬恩这一脉断绝。”朱经致的脸上面露难色,无奈地说道:“皇上,杨酬恩全家株连是皇太后钦定的,擅自改变皇太后的懿旨是死罪啊。微臣…”
我又劝说他道:“朕知道这些,但杨酬恩是大清的忠臣,今日他冒死上谏不是为了他自己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其子孙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是为了黎民百姓,是为了天下苍生。难道爱卿希望大清再这样闭关锁国落后挨打吗?难道爱卿希望大清继续遭受屈辱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吗?难道爱卿不希望国家变革自强以摆脱列强的欺诈压迫吗?难道爱卿不希望一雪鸦片战争后的耻辱吗?”朱经致有些踌躇,我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感化了他,于是接着说道:“倘若天下百姓都知道了杨酬恩为国罹难最后连子嗣都没能保全,这不会让天下忠贞之士都感到寒心吗?总而言之,朕不希望杨酬恩这样的忠臣绝后。况且爱卿是负责此次抄家及行刑的官员,为杨家保留一个男丁于卿绝非难事,难道爱卿希望杨酬恩这样的忠臣绝后吗?”朱经致答道:“请皇上放心,微臣一定竭力办到,绝不让皇上失望,决不让忠臣寒心。”我长舒一口气,说道:“如此朕就欣慰了,毕竟杨酬恩是为了朕才遭此横祸,朕是对不住他。”朱经致说道:“皇上不必太过伤心,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今皇上您青春鼎盛,皇太后却已经日薄西山,这大清朝堂迟早会由您亲政掌权。等到那时为杨酬恩平反绝非难事,如今能够尽力为杨家保留子嗣,皇上您已经问心无愧了。”朱经致的一番话说的我很受用,内心的自责感稍有减轻。因为担心被外人知晓,我也不敢与他长谈,便说道:“既如此,一切就全都托付给爱卿了。爱卿速速归去,以免被他人知晓惹来麻烦。”朱经致这才应声而去,临出门时我又嘱咐道:“路上仔细些,小心被人跟踪。”朱经致点了点头便快步而去。
据听说杨酬恩死的很惨,我难以想象活剐三千六百刀是怎样撕心裂肺的痛苦折磨,我自然是没有见到这凄惨的景象,一切都只是听说而已。第二日杨酬恩一家老少都被处死,连杨酬恩八十余岁的老母也未能幸免于难。好在有朱经致的帮助,杨家保留了唯一的子嗣,留下了杨酬恩刚满月的孙子,得知他还没有名字,我便为他取名“杨承嗣”,意为“承继祖宗,绵延子嗣”。朱经致将杨承嗣寄托在一处乡下人家抚养,我命王晋田偷偷从内帑中拿出一些银子置于那户人家,权当是抚养孩子的费用,如此才可稍安我心。但是一想到杨酬恩忠心耿直却惨遭杀戮期我的心情就又不能平复。恍惚之间我又想起了明朝末年的蓟辽督师袁崇焕,他也是一心为国最后却惨遭凌迟处死,没想到时隔二百多年杨酬恩的命运也是如此。猛然间又想起南宋爱国名将岳飞,七百多年前他也是被宋高宗以十二道令牌召回后杀害。我不禁喟叹:“为何自古以来忠臣难以善终?唉!这大概就是宿命吧,人力究竟难违天命。”我知道这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但此刻我也找不到更好更恰当的解释,就让我如此想吧——毕竟这可以减轻我内心的不安与罪责。眼下我只有两个心愿,一是希望杨承嗣可以平安长大,二是希望自己能够早日亲政掌权。日子就这样过吧,我期待掌权时刻的到来。
文章作者


余味
发表文章16篇 获得10个推荐 粉丝43人
积极向上……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