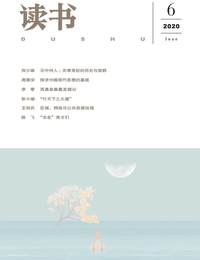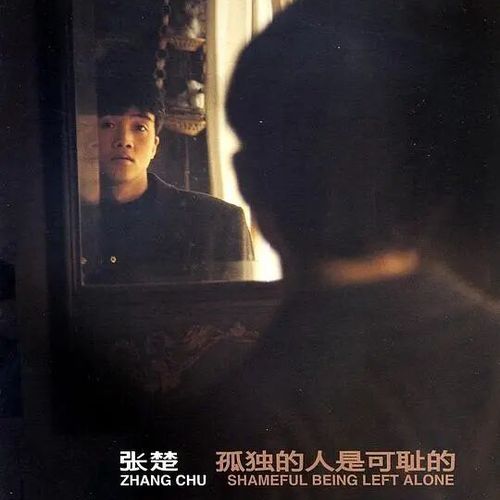“行天下之大道”(上):燕京大学与中外文化的对话
作者:读书
2020-07-02·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664个字,产生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彭小瑜
戴望舒在一九二九年写过《雨巷》,写的是江南春晓的情景:“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到了一九四五年,在香港,受尽战争磨难的他写了《口号》: “盟军的轰炸机来了,也许我们会粉身碎骨,但总比死在敌人的手上好。”
由一九二九到一九四五年,诗人心情变化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经历的艰难岁月!诗人心情背后也隐隐呈现着世界历史难以抗拒、超出个人把握的力量。对照这两首诗,我们再来阅读韦斯特教授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整体的感觉会和作者一样,也就是不得不注意到,这所在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上意义非凡的学校可以说是 “既成功,又失败 ”。而无论强调其成功还是强调其失败,我们只能在世界格局和中国社会的宏大画面中来理解和认识燕京大学。由中长时段来观察,深度和持续的中外文化共融从来没有在现代中国停止过,而燕京大学以及它后来加入的北京大学始终是这一交流以及中美友好关系的高效平台。需要注意的是,燕京和北大所擅长的中外文化对话有相当一部分涉及中西关系,但是从来不局限在中西和中美之间,从来都是拓展到包括亚洲和俄罗斯等国的广泛国际文化研究。这一特色在北京大学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发展中尤其突出。
晚清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有着鲜明的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有着强烈的实用色彩,但是燕京学者以及其他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都注意到,对中华民族复兴具有根本意义的文明对话必须建立在深度的、能够探索问题根源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对中国学者来说,这一对话不可能是单方面期望或要求对方了解和理解我们,一定需要包含我们自己对外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的系统研究。而这一切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爱国救国的社会变革道路的一个侧面。用齐思和先生这位燕京毕业生和教授的话来说(《勇德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之地位及其变迁》,一九四三),就是如何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应用儒家之最高理想于社会公义的追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 ·滕文公下》)
燕京大学的历史并没有在一九五二年停止。燕京的人文学科和部分社会科学学科以及部分理科并入了北京大学,燕园继续作为北大的校园在使用。燕京在此期间对中国学术建设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其文化影响和师生脉络一直留存。这方面的个案很多,我先就我在北大图书馆的见闻,举出一个例子。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20777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