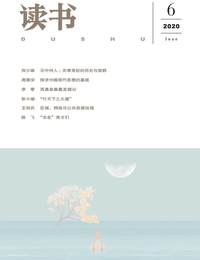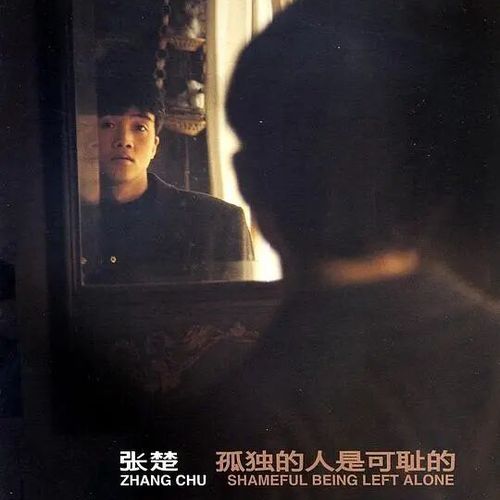虚实之间读西南
作者:读书
2020-07-03·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803个字,产生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钱云
一
一九三一年,《新亚细亚》杂志刊登编辑文章,严厉批判《时报》连载的《西行艳异记》。因为这部书虽号称是作者 “走川西松茂等西番部落 ”的“事实 ”游记,实际上不仅多有讹误,更是一部 “以‘寻艳求异 ’为能事 ”空中楼阁般的 “旧小说 ”。而且,该文作者借此书评还特别提出边疆考察应分为两个步骤:一是 “把对于边疆的 ‘神奇 ’的观念改为 ‘平实 ’的观念 ”,二是 “把考察边疆的普遍游历的观念改为专门研究的观念 ”(《为评西行艳异记答时报的编辑先生》,《新亚细亚》二卷一期)。
两句如口号般的研究旨向,表明该作者有意鼓励现代式的真实且平实的边疆目光,不仅批判以奇、异为核心的旧式边疆观念,更力图将 “旧小说 ”彻底排除在现代边疆研究的视域之外。这正彰显了近代以来边疆研究的两方面趋向:一是于观察中强调 “平实之眼 ”的价值,打破传统 “华”“夷”的阻隔,均以一般之国民而重新认识;二是在选材中偏重真实性为先的史地考证、边政反思、风俗描写,至于专事诡谲奇幻的 “旧小说 ”则难为学者用于实证研究。
可如果仔细审视这一时期的出版业,类于《西行艳异记》之类的“旧小说 ”颇多。如一九四九年广州民智书店、大成书局印行了一本署名林仁超的《琼崖黎洞奇观》,讲述的是作者在海南岛上的奇遇,所记内容虽不至全是荒诞无稽,但作者明显有意挑选奇幻艳丽之事以呈现黎汉间的差异,甚至配图也有意捕捉香艳、猎奇瞬间。因此可以说,严谨真实的研究与奇幻艳丽的小说,一起组成了近代边疆意象的完整图景。虽然这些小说不能成为 “专门研究 ”的材料,但从 “历史语境主义 ”的视角来说,这些 “旧小说 ”的出现并非偶然,当视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边疆兴趣蜂起下的应时之作,虽不具有研究边疆族群的学术价值,但也实在地参与形塑了一般人虚妄的边疆观念。
不过,正如微观史家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在《孤岛不孤》(文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四年版)中讨论如何理解 “非历史源材料”的文学文本那样,在区分真实与虚幻、追溯 “真实历史 ”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奇幻迷人的文学文本中获得什么?金兹伯格在书中就对昆廷 ·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历史语境主义 ”提出了质疑。他以莫尔的《乌托邦》(Utopia)为例,认为不能仅将其视作文艺复兴时期讨论共和政体的政治理论文体,因为莫尔在书中有意地使用了一些希腊语词,是希望能以此提醒具备基本希腊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 “叙述的虚构性质 ”。金兹伯格也借此提醒读者,需时时注意文本背后创作者的意图。
回到西南边疆研究的领域来说,固然虚实文本的辨识与取舍,成就了历史学、民族学对于边域世界的诠释范式。这种范式研究的对象往往是文本中所呈现的 “真实的 ”异质或同质的边域世界,通过现代学者的考证、重建,在读者与写作对象之间建立互通渠道,帮助他们由现实径直抵达文本(无论是传世记载还是田野访谈)所构筑的历史场景中。可是,真实抑或虚构的文本背后,除了作为语境的 “历史”以外,还有一个具有写作意图、个人情感、叙事技巧的创作者。
换言之,同一时代的文本固然有其历史共性,然而亦有其创作个体,正所谓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从此角度出发,记载边疆的虚实不一的文本,在现代研究价值引导下的辨识与取舍固有其意义,但并不能完全消除创作者个体在宏阔历史中的主体性,因而还需探寻创作者写作意图的贯彻与实现。胡晓真在《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下引此书,只标出页码)一书中,以明代有关西南的文本为中心(不仅采用传统文学文本,如小说、诗词、戏曲,也包括其他由文字来表意或喻意的书写记录,如游记、回忆录、志书等),巧妙地抓住在虚实文本背后的创作者,展开了一系列饶有趣味又引人赞叹的文本分析,对重新理解边疆叙事中的虚与实颇有启发。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20777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