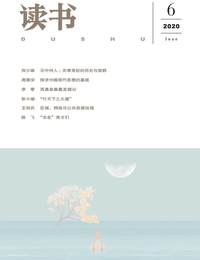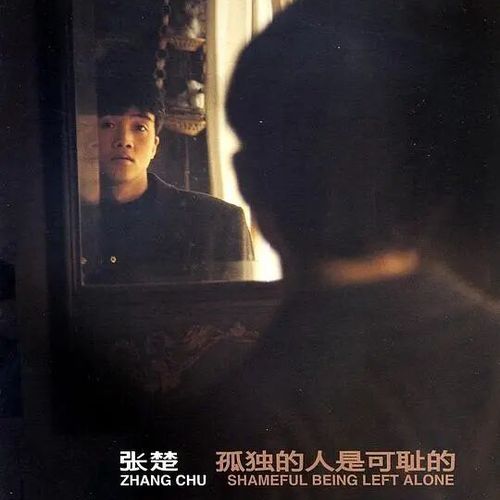“无名”秀才们:重审“哭庙案”之四
作者:读书
2020-07-03·阅读时长12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481个字,产生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陈飞
“哭庙案 ”的官方定名是 “抗粮案 ”。据《辛丑纪闻》(下称《纪闻》)记载,朝廷的最终批复(判决)是:
倪用宾、沈玥、顾伟业、王仲儒、薛尔张、姚刚、丁子伟、金圣叹八名,俱着彼处斩决,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唐尧治、冯郅十名,俱着就彼处斩讫,免籍没。顾予咸免籍没,并免革职。
顾予咸幸免于难,已详前文。十八名秀才全部判处死刑,其中八人并处籍没。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七月十三日,“十案共一百二十一名:凌迟二十八名,斩八十九人,绞四人 ”。巡抚朱国治亲自监斩,分五处斩决,十八人被斩于江宁三山街:
至辰刻,狱卒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一人皆毕命。披甲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
至此 “哭庙案 ”宣告完结。在此之前,除了金圣叹名满天下外,其余十七人皆名不见经传,以至《纪闻》有“十七人者,皆可因圣叹一人而传矣 ”之叹,意谓十七人由于金圣叹的关系得以传名于世,也算是不幸之幸了。
《纪闻》的卷末有十八人小传,除了金圣叹稍详外,其余十七人皆极为简略,甚至 “不详 ”。就目前所见,有关 “哭庙案 ”的文献记载,当以《纪闻》去事最近也记述最详,作者大约与案中人并世同时,目接耳闻或有所交往,而小传如此简略,不免令人疑其别有隐情。十八人大都为 “庠生 ”,庠生亦称 “秀才 ”,可谓是真正的 “秀才造反 ”。作者还特别 “补记 ”了丁观生、朱时若的被捕经过,前者 “偶往府进一呈词,遂罹于祸 ”。后者 “入城拜贺岳父母,初四日,同大章(沈玥)往看哭临,遂被擒 ”。令人在感叹飞来横祸、死得冤屈的同时,也觉得秀才们的行动好似乌合之众偶然之举。作者这样叙写想必有其根据,但也可能是一种 “笔法 ”—因去事未远而有所避忌,故意加以掩饰和淡化。但从 “哭庙案 ”(严格地说,“哭庙 ”和“哭庙案 ”是不同阶段的不同事体,这里为了表述方便,姑且合称 “哭庙案 ”)的实际过程来看,秀才们的行动决非如此。
回顾事发经过,可以清楚地看到:任维初于顺治十七年(一六六○)十二月初一到任吴县县令,立即就 “贪酷 ”异常,倨傲官绅,羞辱士民,严刑催征(钱粮),直至当堂杖死一人,致使 “邑民股栗 ”。这给秀才们的举事提供了理由和时机,但他们并没有立即行动,此可谓“一忍 ”。到了次年正月中旬,任维初公然盗取官粮换钱私吞,这种“典守自盗 ”属罪上加罪,且人所共知。“当是时也,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这给秀才们的举事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和更为强硬的证据,但他们仍然没有立即行动,此为 “再忍 ”。《纪闻》接着说秀才们 “遂有 ‘哭庙 ’之举 ”。这个 “遂”其实是十多天之后,到了二月初一日,“会世祖章皇帝(顺治)哀诏至苏,幕设府堂 ‘哭临 ’三日 ”。哭临的地点设在府堂,地方官绅都要到场,正是秀才们举事的 “天赐良机 ”,但他们仍然没有立刻(第一天就)行动,此为 “三忍 ”。直到二月四日,哭临的最后一天,才群起爆发。据《纪闻》记载:
(顺治十八年)初四日,薛尔张作文,丁子伟(疑误)于教授处请钥,启文庙门哭泣。诸生拥至者,百有余人,鸣钟击鼓,旋至府堂。乘抚、按在时,跪进揭帖。时随至者,复有千余人,号呼而来,欲逐任令。秀才们为何要一忍再忍乃至三忍?原因不难逆推,须联系秀才们的核心诉求来分析。秀才们来府堂 “跪进揭帖 ”意在 “讦令 ”—揭发县令任维初的贪酷并要求惩办驱逐之,但这只是当时可以公开宣明的诉求;其实还有另一层目的,就是抵制太过严苛的催征,但这是不能公开明言的。如何使这一明一暗的诉求 “一举两得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须要具备诸多条件,通俗地说,就是要凑齐天时地利人和诸要件,因而必须等待。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20777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