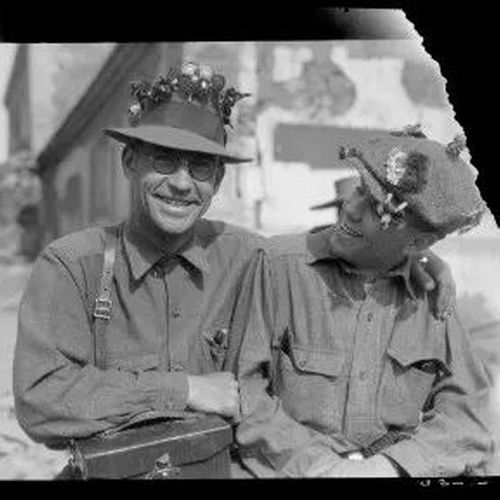成都: 美城并不如烟
作者:朱靖江
2017-07-17·阅读时长8分钟
今年春节姗姗来迟,成都的春天却来得颇早。一厢文殊院外的新年庙会还在火热地招徕生意,另一厢青羊宫畔的游春花会已经雅致地开张。郊外的油菜花黄灿灿地铺张开去,而市井街头的桃花、梨花和玉兰也竞相怒放,粉妆玉琢地点染这座两千多年的西蜀名城。虽然林立的高楼大厦早就让老成都换了新容颜,但透过轻微的雾霭,一缕往昔的烟尘还没有完全落定。
 “如果让我提议成都的五大文化标志地,我认为是少城、华西坝、杜甫草堂、武侯祠和春熙路。”成都老诗人流沙河曾说过,“春熙路是保留成都近代文化的重要地方,它在四川人心目中举足轻重。”
“如果让我提议成都的五大文化标志地,我认为是少城、华西坝、杜甫草堂、武侯祠和春熙路。”成都老诗人流沙河曾说过,“春熙路是保留成都近代文化的重要地方,它在四川人心目中举足轻重。”
作为初至成都的外乡人,东道主一般都会邀你走一遭春熙路。春熙路之于成都,就仿佛王府井之于北京、南京路之于上海一样。步入这条开辟于1924年的“成都第一商业老街”,满眼却是最流行的时尚元素:服饰店、咖啡馆、网吧、酒楼和小食档,填满了花岗岩路面的街道两侧;街心广场中央端坐的孙中山铜像,也被“哈根达斯”冰淇淋和索尼电器的霓虹灯所环绕,多少显得有些时空错位。街头熙来攘往的行人大多是本城的时尚青年和慕名而来的外地观光客,他们或挑拣心仪的品牌时装,或是围坐在“钟水饺”、“龙抄手”的店堂里,品尝几道脍炙人口的成都名小吃。虽说春熙路繁华的商业气息令人称赏,但“成都近代文化”的风韵在外人眼里却仍然莫可名状。
“春熙路的意义就在于它永远是成都最新鲜入时的地方,而非它保存了多少故老国粹。”在春熙路上守着一间玉器铺面的张先生告诉我。的确,从上世纪20年代四川军阀杨森力排众议,拆除废置多年的满清按察使衙门,强使当街的商家住户锯屋檐、缩门面,开通这条象征“新政”的马路之后,这条寓名于《道德经》中“众人熙熙,如登春台”的新式商街便在时代的大潮中独领风骚:无论是民国时期最洋派的照相馆、钟表店、西餐馆,还是改革开放之初个体户云集的喧哗夜市,抑或是今日太平洋百货、伊藤洋华堂等名店纷纷进驻的“西南第一街”胜景,春熙路都把成都人最光鲜的梦想、最活色生香的欲望变成了现实。日本人的飞机炸不烂,内战的萧条拖不垮,文革的狂风也吹不败,一俟春潮涌动,这条并不宽广的街道便再度人流熙攘,恢复它引领时尚的摩登风范。
1920年,美国人约瑟夫·比奇为《国家地理》杂志撰写了一篇名为《东方伊甸园》的游记,记述他在四川成都的见闻。“这是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大城市,”约瑟夫写道,“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其修建得坚固高大的城墙,让我们不由得去猜想这城墙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时隔80余年,成都人欣然将“东方伊甸园”的雅号冠于自己的家园之上,但昔日“坚固高大的城墙”却早已灰飞烟灭。又是承蒙流沙河先生的指点:成都东门大桥附近的青莲上街遗存了明城墙的一段残垣,于是雇车前往一探。
“这算啥子城墙嘛!”出租车司机杨山林把我们送到一片七零八落的废墟边上,睨着那条在旧房和新楼之间狼狈不堪的破墙,从牙缝里呲出了一声感叹。这条三米多高,百十米长的城墙断壁,原先是几户民居的后墙,前两年拆迁的时候显露出来,多亏几位成都文化人的奔走呼吁,总算没有被彻底推倒,就这么在荒草丛中萋萋然地支撑到现在。
成都人对城墙的美好情怀渊源已久,当年后蜀国主孟昶就是在成都的城墙上遍植芙蓉,每逢金秋,繁花似锦,为成都赢得了千年不凋的“蓉城”美名。“我就是在成都的老城墙下长大的。”杨师傅看着这堵破败的老墙嗒然若失,“小时候常在城墙上乘凉、散步、放风筝,好耍得很。1959年的时候,搞‘备战备荒’,城墙被拆掉修了防空洞,啥子都没得了。今天挖到这么一面烂墙又重新当作了宝……”
但在关注成都历史的文化人眼中,颇煞风景的这段残墙却显得意义重大。“这一点点城墙残址太重要了,它是500多年前明城墙东南转角处的墙体。只要它在,就可以考证古成都东门南门的位置。只要它在,和对角处的北较场城墙残址一对应,就可以推断出整个古成都的具体位置。”老诗人流沙河介绍说,“东边和西边的城墙早已不在,北边的城墙也只剩下一丁点,这处残址就是一个重要的地标,也是最后一个古成都的地标!”

距青莲上街古城墙仅隔数百米之遥的耿家巷和龙王庙正街,似乎还保留着老成都最后几分神韵。这片由低矮的古旧建筑组成的老街区虽然残破,却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大块的猪肉被用铁钩子吊在当街的肉铺门口,旁边售卖新鲜蔬菜的三轮车绿油油地摊成一排;水果摊和调料摊毗邻在一起,又紧挨着烟摊、报摊和杂货铺……桐漆斑驳的青瓦老屋旁边,一棵碗口粗的梧桐树孤零零地支撑着天际线;老茶馆缩在院子里,传出哗啦啦的麻将声。幽暗的门廊内,还有磨刀匠跨坐在条凳上,身姿起伏地用油石打磨着菜刀。
龙王庙正街上的行人也不似春熙路上的帅哥靓妹那般时尚,背篓里装着娃娃的妇女们会站在一起闲聊些家事,挑着担子的货郎背影悠然地朝前走着,骑单车卖盗版碟的小贩则把喇叭调得震天响,从街道的这一头喧闹到街道的那一头。街角一家名为“龙回头”的小饭馆生意甚好,花不了几块钱,就可以吃到麻辣鲜香的正宗川菜。就在这么一条不起眼的老街上,时间仿佛故意放慢了步伐,将一份手工时代的温暖记忆残存到今日。
这列老房中最高耸阔大的一个门楼:龙王庙正街41号,就是在成都颇有几分名气的邱家祠堂。这座建于清朝同治六年(1868年)的宗祠院落,原本是非常典型的川西民居,祠堂内曾有三个正方形的大天井,以及五个规模较小的天井,华屋阔檐,庭院深深,彰显出大户人家的非凡气度。昔年每逢农历清明和七月半的时候,来自川西各县的族人便齐聚于斯,共同祭拜邱氏先祖。解放之后,祭祖成了被革除的封建旧俗,邱家祠堂也慢慢败落,先是由公家托管,最终变成了三十六户人家合居的大杂院。
“现今在祠堂里住的邱家人只有一户,邱老汉每天出去打牌,来晚了就遇不到他。”见我们对这座老房子流连不去,在门楼摆卖旧书兼售调味品的李先生善意地提醒我。他指了指门枋和檐口上雕镂的精细花纹,示意我不妨在残旧的木榫结构中体味往昔的华丽气质。虽然从高处俯瞰,邱家祠堂天井院落的大格局依稀尚在,但住户们多年私搭乱盖的砖房早已破坏了庭院的美感,越往深处走,便越觉出一种礼崩乐坏似的悲凉。
据李先生说,从2003年起,政府便计划将这座旧祠堂整体搬迁到大慈寺,作为清代成都宗祠文化的孤本加以保护,但三年多过去,虽然常有拆迁的传闻,但这片老街与老房,连同它的老住户们一道,依然被滞留在成都的“前现代”的气场之中,在四周高楼的环绕侵蚀下,默默沿续着它们杂乱、卑微却又充满人情滋味的市井生涯。

相比这条命运曲折的龙王庙老街,位于成都少城核心区域的宽巷子和窄巷子则是无可选择地步入了一个新时代。少城在公元前347年蜀王开明九世迁都成都时,便得此名。秦灭蜀后,重新修筑的成都城池也分作大城和少城两部分,前者施政驻防,后者平时是商贾云集的经济中心,战时则为大城的前哨与屏障。此后成都风雨沉浮,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满蒙军队入川平叛,驻留成都,在老城的西垣内新筑一城,汉人不得入内,被称作“满城”,但成都人依着旧例,还称其为“少城”。20世纪初叶,清帝退位,天下共和,少城的藩墙被拆毁,城中“鱼骨形”的路网格局却延续下来,以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为代表的老街区,还遗存了兼具川西和北方建筑风格的民居宅院。
随着旅游热潮的涌动,宽巷子渐渐成了“小资”和中外背包客们青睐的落脚点。和北京的后海相仿,这里悠闲的生活节奏与淳朴的民间气息令人慵懒自适,与耆老乡贤们一起泡杯盖碗茶,摆一下午龙门阵,也是浮世生存的一剂清心良药。
但我在丁亥年新春所见到的宽巷子已然是一片将近竣工的工地。新建的仿古宅院雄赳赳地纵列于小巷的两侧,一水儿的灰墙乌瓦制式统一、风格齐整。光润鉴人的棕色木门似乎还能嗅到油漆的味道。虽然洋灰路面还没有最后完工,一些竹椅茶桌已经当街摆起,招邀着巷口寥落的几名行人。
“整条宽巷子还剩下四个老门楼,其他的都拆掉修成了新房。”一位浓眉大眼的中年男子见我有些茫然,主动过来与我搭讪。这位名片上印着“民间飞刀绝技艺人”的汪明生先生三代世居于宽巷子,直到前两年政府和开发商要将宽、窄巷子“打造成成都的第一会客厅”,他家才从这条老街搬到了倒桑树街,但汪明生每天还是会回到宽巷子的路上,和几个同样眷恋不舍的老住户一起,围坐在一张方桌前喝几泡茶,打一下午川牌。
根据成都媒体的宣传介绍:“宽、窄巷子片区的北侧将集中形成传统的客栈、会馆、商务会所、旅游购物区等;西侧将主要修建旅游接待区域,集中大量的茶楼、酒吧,并规划一个五星级的宅院式文化主题宾馆……片区中心区域的综合性非常强,将拥有酒吧、茶楼、展演中心、艺术聚落区域等。”这幅“老成都底片,新都市客厅”的宏伟蓝图,的确有着令人震撼的规划雄心,唯一的疑问是:老巷子里的原住民和他们世代安享的传统生活,就这么烟消云散了吗?
汪明生精通各种用小刀削水果皮的绝活,上过电视和报纸,也算是宽巷子中的小巷名流。他一边向我展示他单手削金橘的手艺,一边喃喃地讲述着往日里街坊四邻彼此关照,互相帮忙的旧事。旁边打牌的老婆婆忽然插句话说:“就算是要把宽巷子和窄巷子修成旅游区,便非要把我们这些老住户都迁走吗?空出来的老巷子留给谁住呢?”
我实在无法回答这个时代性的大问题,甚至难以衡量这场席卷成都、乃至整个中国的“旧城改造”洪流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一桩惠泽后人的善举,还是利益驱动高于保护原旨的一招盲棋。在宽巷子隔壁的窄巷子深处,一座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老宅院门口,依然悬挂着“花茶二元,毛峰三元”的茶铺招牌,院内的几桌茶客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安详地打着麻将,似要将老成都的悠闲风度保留到最后一分钟。
“成都总是要改变的,这任谁也拦挡不住。关键它的发展是否对得住历史与未来。”十年前来成都发展的重庆人周渝坐在自家开办的印度音乐餐吧里,语调铿然地下了断语。如今,遍布在成都大街小巷的酒吧、歌厅、咖啡馆早已取代了昔日茶馆的地位,成为成都人消闲娱乐的最佳去处。高大现代的写字楼矗立在“镗耙街”、“暑袜街”、“琴台路”之类名称古老的街道上,虽不洋派,倒也折射出几分古今辉映的妙趣。沿着蜀都大道径直向南,新建筑日渐回归到绵连千载的川西营造传统,与自然的节律翕然合拍。
建城两千多年来,成都从未更改过她的名字,却因着战乱与升平,不断地转换她的身姿与容颜。虽然这座老城早已不再是杜甫笔下“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古典家园,但只要它车水马龙的街道两旁还容得下几张竹椅,端得出数盏茶盅,挂得起一幅“花茶二元,毛峰三元”的硬纸牌牌,老成都的血脉终将随着府南河的流水,四时不废,长宜子孙。
文章作者


朱靖江
发表文章22篇 获得15个推荐 粉丝273人
视觉人类学者,民族志电影作者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