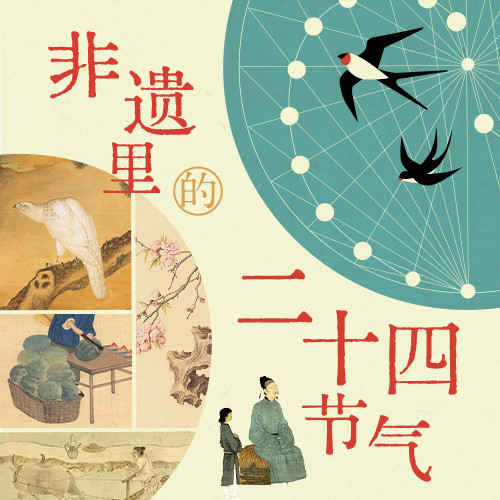陷落的与永恒的
作者:读书
2019-04-12·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748个字,产生1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张屏瑾
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的结尾,著名的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也许就为了要成全她,成千上万的人的命运都改变了。张爱玲写这小说的时候还太年轻,《传奇》《流言》里少不了年轻放狠的态度,说不尽的苍凉大多挂在嘴上,战乱年代是历史打了个盹,因此“海派”得以屏息定神,凝视当下,倒反看出许多“人性之永恒”来,即使是不彻底的。
这大概就是小说家的梦想,在一些极为特殊的东西中找到通向真理的路途,特殊可以幻化成各种奇异的形式,进而生出无穷的艺术创造的可能,而真理,谁不想一窥其面目呢?
不过中国人的爱智总是离不开对历史的把握,在汉语世界里,还没有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十九世纪末海派乍一兴起,跟这种泛历史主义的习惯形成了一些冲突,舶来品、无根基,为一时的热闹、痛快、不讲章法,甚至不择手段,这是当年“京海论争”时人们对于海派的非议。实际上,历史本身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看待历史的方式当然也会随之生变。海派杂糅无数悖反条律:既与刚刚诞生的市民理性有关,也跟情/欲纷纷扬扬的碎片有关;放眼世界胸怀天下,也抖不尽鸳鸯蝴蝶小家闺阁;孕育出激进的抗争意识,也被各种各样的拜物教占领。从远处看,上海是中国历史的沧海一粟,是飞地,也是“非地”(non-place)——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方,朝近处看,从这里开始讲述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故事是必然的,如果在传奇之外,还有可能用某种追求真理的眼光来探询这座城市背后的本质的话,那么海派传人也并非不值得一当。
在这个意义上看,王安忆跟海派小说的渊源关系就比较复杂,为了突破洋场中各种表象之间的悖论,她总是采用正反合的方式来讲故事,总是洋洋洒洒,总是力求辩证。她多次尝试用长篇小说来讨论,在这座城市里,究竟什么东西在对我们的生活起决定性的作用,什么是主流,发生了怎样的角力,结局为何,余韵怎样,各种力量声部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须得通过实际对象来把握,第一种对象当然是人,历史中的人,城市里的人,不光是故事主人公,而且是高度特征化的形象,落实了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当代英雄”,这宛如回到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流。但是,自二十世纪起,有关人的叙事限度越来越大,荒诞丛生,一地鸡毛,风流云散。相反,物质的历史变得越来越重要,仿佛物比人更能承担命理天道,比易朽的肉体更能承载长时间去芜存菁的考验,显现出某种永恒的答案,新文化史的流行就是一个明证。当然,此物首先得是机械复制时代仍有灵韵的物。在王安忆这里,二○一一年的《天香》写出一部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风俗文化谈,而二○一八年最新的长篇小说《考工记》的主角也是一栋年久失修的古宅,从晚明而来的灵韵最终流浪衰败于二十世纪。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20764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