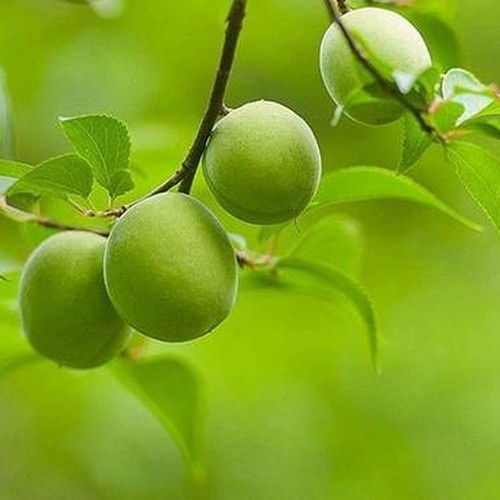谁心里没有一个为了生活被迫放弃的梦想呢!
作者:玥超
2019-07-03·阅读时长5分钟

生而为人,都有梦想。对于素以失败的理想主义者聊以自慰如在下者而言更是如此。三联中读APP上主持"戏聚时刻"的那个年轻的小同学安妮在vol.2里不经意的一句"谁心里没有一个为了生活被迫放弃的梦想呢",于那天我费尽心思偷得的一线晨光里,还是深深地戳到了我于膏肓之间隐匿的抱憾,就是音乐!
关于音乐的启蒙,确切无疑是来自位于两个偏僻村庄缝隙里的那所简陋的乡下小学,但至于是缘起于给我们代过课的献军哥的那把破旧的弦子(二胡),还是如我先前一样瘦削似我如今一样苍老且戴着厚瓶底一样近视眼镜的凤朝老师,终究是不得而知。记忆犹新的是某个冬天漫天飞雪时放学的傍晚,背着母亲用碎布片拼缝成的百衲衣一样的书包,尚且未知愁滋味的我仰着小脸嗷嗷乱叫着一边兴奋不已地往家跑,一边似唱非唱似念非念地嘶喊着,"下雪了,好象有人在天上撒白糖"。
蓦然回首,我毕生的快乐似乎就这样绝无“携行”全部“后留”给了那些个不谙世事的童蒙时光。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所谓的懂事,便是意味着开始体验到了挣扎着生存的阴郁与悲凉。记得当时跑过油印爷家门口时,一扭头正好看见身形瘦小的油印奶一个人默默站在低矮的墙头后边也看到了我。虽然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可老人家慈祥的笑脸却永远地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而这幅遥远却始终清晰着的影像,伴随着彼时"思无邪"一样的谈不上欢唱的叫喊,勿庸置疑地成了我爱乐好唱的滥觞。

除此之外,便是村里随处都能听到、身边老少爷们儿媳妇姑娘都能哼上几句的戏曲唱段,诸如曲子、梆子以及并非越剧之越调之类。而我至今都佩服我自己的是在记忆里我们那个又穷又小的庄子里唯一一次唱大戏时,约摸也就是小学三年级时小小的我,竟然坐在泥巴地上全神贯注地看了大冷天晚上的一个全场,戏名《望月楼》,说的是某朝某代某个忠臣良将全家为奸佞所害,幸存的老八长大后报仇雪恨的传奇篇章。俗套的故事与情节,熟稔的唱腔与旋律,草台的班子与扮相,然则是民间戏曲里延宕的中国百姓朴素情感的祈祷与向往。
除了春夏时节用嫩柳枝拧抽去除木质削成的柳笛,口琴应该算是我平生拥有的第一件乐器,可是花了五块钱专门托人从市里代购回来,记得是敦煌牌回音款的,虽然并非是我期望的重音,可也是了却一桩奢望。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五块钱绝对也不是个小数目,足以想象老父亲对我这些貌似不着调的爱好多么地慷慨解囊。平时奏唱的大多是时下流行的《彩云追月》、《泉水叮咚响》还有《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等,这些曲子无以例外地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以至时时让我由衷地对音乐世界无限地心驰神往。

而若干年后最后一次复读时,连真正的钢琴都没有看见过的我这个为了跳出农门的落榜文科生,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实则自负地把音乐当成能抓到的最后一根稻草,孤注一掷地转而又报考了本地师专的声乐专业。尽管我把五线谱抄得被老师赞为跟刻印的一样,乐理知识背的滚瓜烂熟,视唱与听音得分达优,可惜这些都不是重点,因为我那"吊嗓儿"练成慢性咽炎至今说话多了嗓子都会嘶哑难受的半调子声乐专业,终究还是没能把"半路出家"的我带进音乐的殿堂。
于是乎,再度落榜后可想而知的走投无路之下,满怀惆怅郁郁寡欢地用从大嫂娘家借来的一把二胡"拿腔捏调"地拉了几个月的《满江红》以后,最终还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夜登上了开往戈壁深处的绿皮火车决绝地离开了沉默无计的二老爹娘。以后的那些年,在西北,当过几个月军乐队里的长笛手,还特意去某歌舞团试图拜师深造,但最终因为无法赖以生存还是忍痛选择了放弃;在华南,给某个演出队跑龙套时,摹仿痕迹甚重的作词写曲未曾想竟被可可队长编成男声小合唱参加了有关部门的文艺调演,以致令我雄心勃发甚至想要请人推荐哪怕是自费也要去星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回忆起来那时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赧然汗颜得现在都想撞墙!

但关于音乐的终极梦想,始终是我心灵深处的亚历山大的宝剑也斩不断的心结。这些年手里乘兴而至的各种乐器,都能凑成了一个小型乐队。长笛是标配,最爱的竹笛曲的梆的好几根,口琴升级成最宽音域还特意弄了蓝调的布鲁斯,经典的百乐牌手风琴大小各一,它们共同的特点便是虽然价值不菲却坚定不移地荒废着各自的荒废。及至而今,只剩下唯一的欣慰是,当年一二十岁了连钢琴都没有见过的那个迷恋音乐的家伙,终于可以不用落寞地流连于人家楼下只为了聆听清澈的琴音在飞舞的指间流淌。
众所周知的后来的后来,便是莫可名状辗转反侧的现在,散落于天南地北年轻时的难兄难弟,机缘巧合相聚时,总是会言及以前跟我学唱了什么歌曲以及一起拉歌赛歌时的斗志昂扬。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当年的那个忧郁干瘦的教歌员心里装满的只有如何好好生存下去的卑微念想,因为好多生歌新曲对照简谱一句句教会了他们以后,心不在焉的我自己都还不能够地完整地唱上一遍,比如当年阎维文的《一二三四歌》;他们更不知道的是,现在表面上看起来自在安闲的我,在"原以为翻过了一座陵,谁知道还有一道冈"的不为外人所知所解的生存窘状里撒开了脚丫抡圆了膀子再也是扯不上了我心里深藏的那个音乐梦想。

扪心自忖,来自小地方,本是小人物,得过小日子;欲风流,难称才子;虽落魄,亦非文人。只有中学语文课本文字基础的在下,近些年竟然一度"沦落"至"想要唱歌不敢唱,就是哼哼也得东张西望"般的“荒谬荒唐”。为了躲避与化解日常诸多嘈杂纷扰,"踏遍青山人未老"却是心已苍的我,只能是每天早上五点钟左右就得起床才能够争取到个把小时纯粹是为了自己而非单纯为了活着的寸金时光,真得庆幸还可以觅得一份心境的静清和唯有阅读与码字才能获得的最后舒畅。
噫嘻!曾经三十未能而立,四十尚且多惑,如今五十仍然难知天命。所谓天随人愿,往往是惺惺相惜或者自欺欺人式的一厢情愿;而所谓知足常乐里的那个"足"如果根本就不你的内心所向,不管它看起来是何等丰厚的"足",又怎么能把由衷的笑容镌刻在脸上遑论心上!人生之路千万条,最终会走上哪一条谁也不能说了算。世事沧桑,真的是就像那个十分敬业的知名戏剧媒体人安妮小同学所言,环顾四周,又有谁不是渐行渐远着各自珍藏的私家梦想!唯愿后者来者,回首再无感伤!【图片来自网络】

文章作者


玥超
发表文章108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72人
落榜文科生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