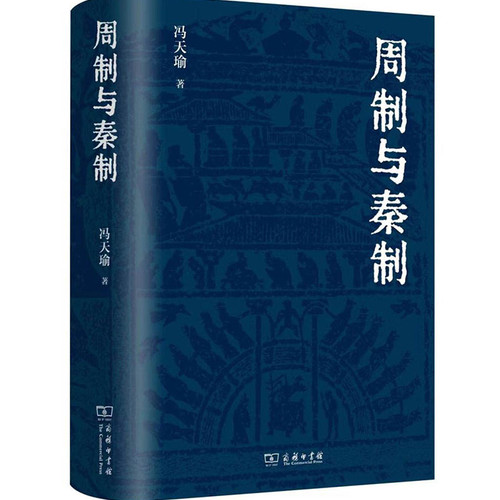现代性已经走投无路了吗?
作者:维舟
09-29·阅读时长9分钟

“这本书我要是能卖出去500本,我就真的很满意了。”
马克·费舍在出版这本《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时曾这么说道。这不完全是自谦,毕竟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边缘人(他曾经的主要身份是乐评人),他很难对市场反应抱有多高的期待,事实上,直到他去世,没有人评论过他出版的任何一本书。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这本看起来对公众甚至略有点晦涩的小册子,居然赢得了无数普通读者的认可,连一向刻薄的哲学家齐泽克也称赞这是“对我们所处困境的最佳诊断”,为什么?
我想是因为,好久以来,都没有人像它这样对当下盘根错节的时代症候给出这样清晰的文化诊断了,有时你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哪里不对劲,在这里则一语道破。当你感到前方无路可走时,就太需要这样一份蓝图,至少让你知道大概可以朝什么方向走。

没有改变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早有人发现,虽然发达国家的繁荣富裕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地步,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并没有变得更幸福,倒是有一种空洞的无意义感、无聊感不断弥漫开来,抑郁症几乎成了现代社会的流行病,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更折磨人的是,你被告知这一切都只能由你自己负责,因为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所有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而这种自责又进一步加剧了抑郁——此时,如果你感到抑郁,那你最好去看心理医生。你甚至搞不清楚那种困境是谁造成的,又是怎么造成的,只能默默忍受或排解,毕竟,“不然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马克·费舍告诉你,个人的精神痛苦从来不只是个人的,它也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有关。事实上,让你认为你的情绪健康始于并终于你的个人心理戏剧,并让你自行消化所有压力,这本身就是当下最突出的社会景象之一。
撒切尔夫人当年曾有一句名言:“没有什么社会,有的只是个体的男性和女性以及家庭。”直到二三十年后,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将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推到世人面前,很多人才逐渐明白过来这意味着什么:原先那种作为共同体意义上的“社会”,已经被一种私有化的形式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合作、互动一点点萎缩,而个体成了“孤独的权利持有人”,公民变成了消费者,似乎我们活着的全部追求就是更多的金钱、更多的面包和更多的马戏——如果你还不满足,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当这成为一种时代症候时,它就不再仅仅是孤立、偶发的个人问题了,那必定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最为重要的一点,恰恰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排除了一切政治化的可能,而把社会问题私人化了:如果酗酒、吸毒、暴力犯罪都被看作只是个体的心理疾病或原生家庭所致,那么就不用去追究社会系统的因果关系了,不用去探讨那是否由社区贫困、政策失误所导致,当然也就不会有随之而来的反思和积极行动,改变又从何谈起?
可想而知,一个没有改变的社会必然是让人绝望的,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希望,有的只是停滞:“未来”毫无意义,明天和今天也不会有太大不同,没什么值得激动人心的,日子只是这样不断地循环往复。所有人的精力与其说是在寻求“变好”,不如说是为了竭力防止“变坏”,并且,不会有人帮助你,你只能靠自己——相应的社会机制是缺失的,还责怪你所有问题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这种困境让无数人受苦:“使我们受苦的,是受困于自身——困于一个人人受困于自己的感受、受困于自己的想象的个体主义世界。”实际上,人们已经太久看不到能怎么改变,正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言,当代年轻人已经失去了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而“更喜欢思考怎样在这个无序的、不可预测的、让人不舒服的世界中,为自己和家庭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
不仅如此,人们甚至普遍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不断改善的进步主义似乎既过时又不现实,如果未来和当下也没多少区别,那么现状岂不就是生活的常态?还不如别折腾了。马克·费舍强烈批评这是官僚制“抗拒一切修正或质疑”的本性使然,另一些人则抨击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太过平庸而缺乏改变的政治意志,然而,问题的根本还不仅如此。
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前些年所言,西欧社会正苦于“未来的枯竭”,原先那种乐观的进步、繁荣信心,正在现实的危机面前急剧退缩,从上到下都弥漫着进退失据的不安全感和束手无策的无力感,难以应对未来的挑战——人们不知道能有什么指导自己当下的行动,走向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而是被“困在了当下”。

现状的霸权
回头来看,1999年上映的《黑客帝国》并不是关于未来的科幻电影,它映射的就是我们的现实: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无形但无处不在的控制网络之中,一切都已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个人对此无能为力,你甚至不知道该去反抗谁、该怎么反抗。当然,更多人根本就不想反抗。“社会”(society)这个原本人与人组成的有机体,此时蜕变成了由无法逃避的强制力掌控的“系统”(system)。
这样一个系统的运行倒未必全然依靠强制,更确切地说,它依靠的是让所有身处其中者内心的绝望感:除了顺从,别无更好出路。即便你隐隐约约看到一些迹象,察觉现状正在温水煮青蛙式地慢慢恶化,但没有人去反对,不仅是因为分散、孤立的个体无法联合起来采取什么行动,也因为人们想不出还能怎么做。
所谓“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普遍的感觉:“资本主义不但是西方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系统,而且,如今,就连给它想象一个合乎逻辑的替代选择也不可能了。”奇怪的是,这种如今看起来透着绝望、烦闷的感觉,起初却是相当乐观的:在冷战结束之际,弗朗西斯·福山就曾欢呼这是“历史的终结”,意味着西方现代社会的模式已经被认可为唯一的、最终的选项,历史不再演进了,仿佛天堂里只剩下无聊的幸福。
确实有不少人被他说服了,他们或是积极拥护现状,又或是消极认同现状,但背后的心态都是宿命论的变种——认命吧,现实如此,现状就是最好的,别幻想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了。在这样的社会里,现实主义已取得了至高无上的霸权,人们对未来缺乏想象力,因为他们认定未来没有任何新东西,何况为什么要去设想明天?只要当下“看起来不错,感觉上良好”就行了。然而,没有现实批判就没有思想,人生也没有意义,因为“意义”必然是超越吃穿住用这些本能享受的。
德国哲学家尼采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幕,当他喊出“上帝已死”时,就意识到随着最高价值的退场,人也就丧失了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只能受本能驱使,满足于俗世的“幸福”之中。这种“末人”(der letzte Mensch)意味着现代化最终走向人类生活的彻底降格,人们不再有高贵的追求,理想沦为笑柄,也失去了超乎世俗的价值观来衡量、引导自己的行为,此种平庸性将掏空人类生活的更高使命,“自由”被庸俗化地理解为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看自己想看的娱乐,而不再指向内在心灵的解放。
在此有必要补充的是,这不仅仅是对现状的屈从、精神的退化,还是对启蒙精神的反动:本来,启蒙的理念就是旨在将人从神学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以自主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开辟进步的道路,然而现代性发展到今天,似乎已经走投无路:不断进步的信念正在丧失,社会的发展要么是小修小补,要么沦为现状的重复,在全新的超稳定结构之下,一切变革看起来都不可能了。现代人有了空前繁荣的社会和发达的技术,但却从未如此对自身的力量没有信心,连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完满,都不清楚。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马克·费舍对现状发自内心地厌恶:那样一种没有变化的安稳生活对他来说不仅是沉闷压抑的,从根本上来说甚至是反人性的,因为那相当于否定了人的可能性,压制了他们追求自我超越的冲动,一个有理想的人可想会活得十分痛苦——你任何超越现实、批判现实的想法,最有可能得到的答复大概就是:“现实点吧!”
他的抑郁,恐怕也与此有关,但从另一面来说,他实际上又是相当乐观的,因为他始终坚信乌托邦才是现实的,强调自己不会放弃对一种“新的人性、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爱”的持续承诺,因为他相信批判现实的超越追求不仅有可能、有必要,而且能够实现。
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路
在金融危机之后不久的2010年,马克·费舍就呼吁:“后福特主义的路走到头,保持向前看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前面似乎什么也没有的时候。”
如何才能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路?那首先就需要一种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曾指出:“与动物相反,没有什么本能的东西告诉人必须做什么;而且与昔日的人相反,也不再有什么传统的东西告诉今天的人们应该做什么。”反过来说,也只有人才具备这样可贵的能力:通过批判思考,行动起来改变现状,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
因此,反思“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理论探讨,也是在召唤行动,然而,在一个普遍认同现状、孤立的个体又深感无力的社会,那可想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不仅需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即便反思了现状,那未来就能自动浮现了吗?
本来,当一个社会感到陷入困境、走投无路时,通常能凭借的就是主流之外的思想资源:异域、传统、亚文化,通过引入这些原本边缘的理念(一如文艺复兴挖掘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启蒙哲人引入东方思想),来达成对现实的批判。正所谓“边缘是未来显现之地”,在现代社会中,也往往是在这些边缘地带有着最丰富的多元文化,当然也可以“到一切时代去寻找失去的可能性”,然而,“历史的终结”本身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征服了所有边缘地带,已经很少人还相信那里能出现更好的替代选择了。
如果“乌托邦已死”,那是否也就没有什么未来还值得期待了?
当然不是。马克·费舍在书中一再强调的就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一霸权意识形态看似牢不可破,但其实只是一种脆弱的幻象,未来仍然在我们自己手中,“需要同时牢记以下两点:资本主义是一个超级抽象的非个人结构,以及没有我们的合作,它就什么也不是”,“我们必须把历史终结的漫漫长夜当作一个巨大的机会来把握。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压迫性的无处不在意味着,甚至替代性的政治和经济可能性的微弱之光,也会产生超乎寻常的巨大影响”。他因此坚信,“在什么都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突然一切又变得可能了”。
在这样一个未来到来之前,首先当然需要思想上的觉醒。不过,吊诡的是,虽然他批判了现代性已走入死胡同,但他的批判本身恰恰证明了这一社会的活力仍在:它至少仍能催生出这样的自我反思精神,社会也能予以积极回应。按《自反性现代化》一书的观点,正是这“构成欧洲活力的根本:即通过激进的自我批评和创造性毁灭进行自我更新的能力”。这就是现代性的自反性: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原有的基础便越是受到消解、改变和威胁,但只要这个社会仍有能力自我调适,它就有未来。
如果你想象不出来那个未来是什么样,那很正常,但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一点:在这个“乌托邦已死”的时代里,乌托邦仍然是一种必要,因为没有想象,未来不会自动浮现。一旦人们都认可了未来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就会成为一种自动实现的预言。从这一意义上说,想象力是当下最稀缺的品质之一,因为它寻求超越现实的改变,伴随着勇气和行动。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顺应现实,放弃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只是那种选择不带来任何改变,但我们不能仅仅如此活着,借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话说:“我们没有选择,但我们不得不选择。”
文章作者


维舟
发表文章32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417人
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