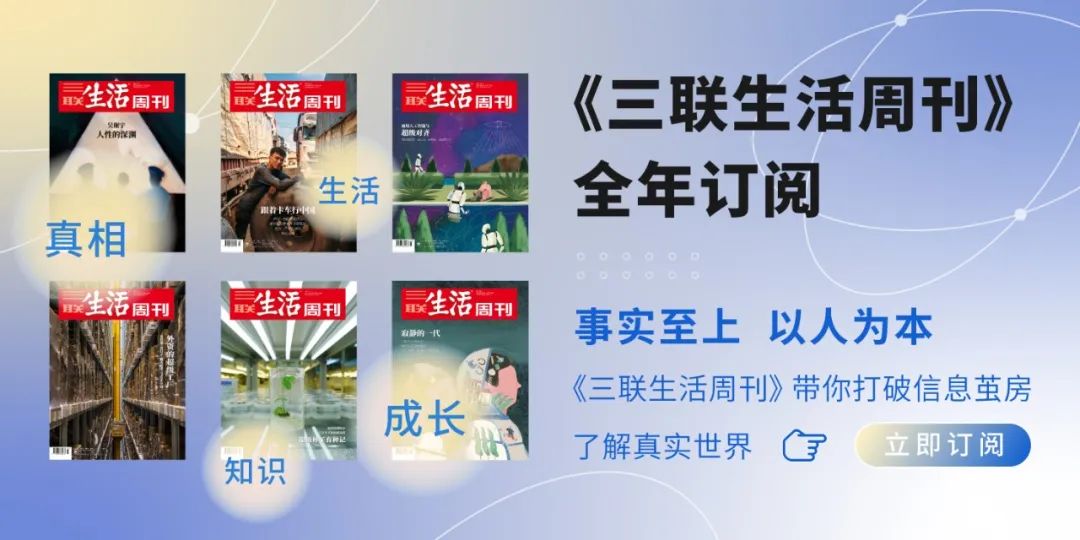这部国民级顶流谍战片,何以爆火十年?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9-10·阅读时长24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15年8月31日,《伪装者》开播,至今十周年了。这部偶像谍战剧,豆瓣8.6分,是近十年来国产剧的一个经典作品。在《伪装者》之后,“偶像+谍战”一度成为风向,却没有任何谍战剧再度复制它的成绩。
《伪装者》能火,偶像元素是锦上添花,它本身是很扎实的谍战剧作品,“谍战为骨,亲情为魂”更是扣人心弦。可惜,之后模仿它的偶像谍战剧,大多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将偶像置于创作中心,谍战部分本身并不合格,偶像元素也是无本之木。
从2015年至今,也恰好是流量时代盛极而衰的过程。偶像/流量不是原罪,但如果没有好的故事作依托,如果不能善用“偶像”,迎来的只是剧集的坍塌。重温《伪装者》,也是重申一种正确使用偶像的范式。
文|曾于里
2015年8月31日,《伪装者》开播,至今十周年了。这部偶像谍战剧,豆瓣8.6分,是近十年来国产剧的一个经典作品。在《伪装者》之后,“偶像+谍战”一度成为风向,却没有任何谍战剧再度复制它的成绩。
《伪装者》能火,偶像元素是锦上添花,它本身是很扎实的谍战剧作品,“谍战为骨,亲情为魂”更是扣人心弦。可惜,之后模仿它的偶像谍战剧,大多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将偶像置于创作中心,谍战部分本身并不合格,偶像元素也是无本之木。
从2015年至今,也恰好是流量时代盛极而衰的过程。偶像/流量不是原罪,但如果没有好的故事作依托,如果不能善用“偶像”,迎来的只是剧集的坍塌。重温《伪装者》,也是重申一种正确使用偶像的范式。
文|曾于里
“谍战为骨,偶像为皮”
今日我们所熟悉的“谍战”,是新世纪之后才流行的概念,并经由《暗算》《潜伏》《悬崖》等一系列经典的谍战剧,逐渐形成一套稳定的类型化体系。时间背景上,谍战剧大多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背景;人物塑造上,主人公通常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需要通过伪装、切换身份在敌营潜伏,并通过主人公面临的生死抉择,展现信仰对人物行动的支撑,传递忠诚、牺牲等价值观;情节特点上,强节奏、重逻辑,充满悬念与智斗……

《暗算》(2006、豆瓣9),《潜伏》(2008、豆瓣9.5),《黎明之前》(2010、豆瓣9.2),《悬崖》(2012、豆瓣8.4)等经典谍战剧,都是以中年硬汉为主人公,“英雄性”置于“人性”之上,他们隐忍、冷静、谨慎、果决、忠诚,没有什么太个性化的标签,柳云龙、张嘉译、孙红雷等实力派演员是谍战剧专业户。谍战剧也都是严肃正剧,比如《潜伏》中,余则成的服装以中山装、灰色西装为主,翠萍的旗袍也多为素色款式,剧集色调偏冷暗,强化压抑、紧张的谍战氛围……作为“客厅电视剧”的谍战剧,在很长一段时间更多受到中老年观众的喜爱。
2015年《伪装者》播出后,收获了现象级的反响,在湖南卫视播出时以极高收视率牢牢占据榜首,也在互联网上引发广泛的讨论,胡歌凭借《伪装者》和紧接着的《琅琊榜》迎来事业的第二次巅峰,靳东、王凯、刘敏涛、宋轶、王鸥等演员纷纷走红。《伪装者》“谍战为骨,偶像为皮”,拉开偶像谍战剧的帷幕。
《伪装者》将偶像派演员置于核心位置。胡歌饰演的明台,一出场就是富家少爷,任性调皮,也机敏勇敢,与《潜伏》余则成、《悬崖》周乙等人的气质截然不同。靳东虽然是中生代演员,但彼时他人气还没有爆火,他饰演的明楼具有多重身份,运筹帷幄,气质儒雅。王凯饰演的明诚,帅气忠诚,与明楼几乎是形影不离……



《伪装者》不仅是彼时谍战剧颜值最高的一部,还是“最时尚”的一部,服化道彻底打破了传统谍战剧的朴素感。明台的西服、风衣、马甲等服装造型30余套,紧扣富家少爷与特工的双重身份,兼具帅气与功能性;明楼以风衣为标志性着装,搭配剪裁得体的西装,凸显出大哥的沉稳气场;明诚也几乎是西装与风衣造型,贴合明楼左臂右膀的干练气质。
女性的妆造同样极致精致:王鸥饰演的汪伪特工汪曼春一头时髦卷发,一抹艳丽红唇,宋轶饰演的于曼丽总是婀娜的旗袍造型,刘敏涛饰明镜的服饰造型端庄贵气……


虽然把谍战剧拍成了“时尚秀”,但《伪装者》倒也没有脱离具体语境。剧中的明家是上海滩声名显赫的富豪之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极高的社会地位,华丽的服化道是视觉消费,也符合人物的身份。
视听语言上,《伪装者》既有传统谍战剧冷硬、压抑的部分(比如明台在军统受训部分),但在“明家日常”部分,以及明台与于曼丽、程锦云等人的互动中,剧集是非常时尚的拍法。比如明台与于曼丽联手刺杀汪曼春的叔父汪芙蕖这一场戏,镜头毫不吝啬地用慢动作和特写聚焦明台剪裁精良的西服勾勒出利落身形以及身着旗袍的于曼丽的摇曳生姿,他们并肩行走时,仿佛T台秀场。仰拍角度强化了角色的气场与魅力,子弹呼啸与衣袂翻飞之间带着精心设计的节奏感,赋予了传统谍战剧所不具备的摩登气质,俨然民国版“007”。

传统谍战剧以任务驱动为核心,《伪装者》在保留高强度悬疑叙事的同时,大幅提升情感戏的比重和细腻度。明家姐弟的亲情、明台与于曼丽的感情、王天风与明台的师生情,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CP,特别是“楼诚”CP(明楼与明诚)热度极高,是当年微博上最火的CP。《伪装者》充分利用CP粉的自来水功力,鼓励粉丝各种二创,极大提升了年轻观众的观剧热情。当时新浪微博一个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伪装者》女性观众占比超过65%,16到30岁的观众占比76.35%,打破了传统谍战剧的年龄圈层壁垒。
“谍战为骨,亲情为魂”
如果以为《伪装者》能火,靠的仅是偶像颜值和CP乱炖,也是极大的误解。偶像谍战剧仍旧是谍战剧,做好谍战剧的本分,甚至还能有所创新,才是《伪装者》成功的前提。

谍战剧最显著的特征,是对“身份”的多重构建。特工要潜入敌方阵营传递情报,必须依托伪造的身份,若没有这层伪装,他们的立场会立刻暴露,所有行动都无从展开。而主人公身份的伪装与掩护、暴露的危机与危机的解除,都是推动剧情转折、深化主题的关键节点。
传统谍战剧的核心人物多以“双重身份”构建戏剧冲突。如《潜伏》中的余则成,表层身份是国民党军统局(后改为保密局)天津站的机要室主任,实际身份是潜伏于敌营深处的中共地下党员,《悬崖》中周乙的公开身份是伪满洲国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真实身份是中共情报人员……《伪装者》则在身份这一核心元素进一步发挥,以明家为核心,构建起全员多重身份、全员“伪装者”的新范式。

明家四姐弟都具备双重甚至三重身份。大姐明镜是明氏企业董事长,也是资助中共的红色资本家。明楼的表层身份是汪伪政府财政部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特务委员会副主任(需应对日本特高课与76号的监视),第二层身份是军统上海站情报科上校科长“毒蛇”,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上海情报组组长“眼镜蛇”,三种身份需无缝切换,稍有疏漏便会暴露,这是传统谍战剧单一身份人物难以呈现的。明楼与明诚是是主仆、上下级、兄弟和知己的关系,明诚更像是明楼的执行者。明台承担了谍战剧中“成长”的主线,从最初的明家三少爷、香港大学新生,到被王天风绑架后成为军统特工,再到后期转向中共地下党,身份转变过程中也是他的信仰挣扎与选择过程。
“全员伪装”构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身份矩阵。身份越多,暴露的风险呈几何级数增长,而明家的人不仅对外得防止身份暴露,也得向家人保护自己的身份,甚至有可能与至亲拔枪相向。这是《伪装者》叙事视角上的创新——谍战与亲情的博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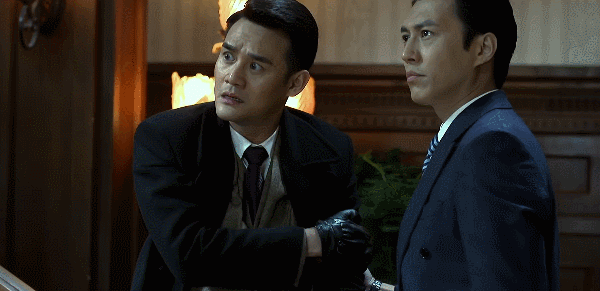
明家姐弟都是“伪装者”,而他们又是如此相亲相爱,“明家日常”是《伪装者》中最有魅力的部分之一。在传统的谍战剧中,主线是敌我交锋与任务执行,家庭亲情多处于辅助性、边缘化和工具性的地位,虽然常常有“假夫妻”到真感情的变化过程,但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家庭场景是缺失的,没有家人围坐的餐桌,没有姐弟间的斗嘴,没有长辈的叮嘱……这种设置固然可以保证谍战主线的紧凑性,但人物的情感世界和日常生活被大幅简化,牺牲了叙事的丰富性和人物的烟火气。

《伪装者》填补了的谍战剧中家庭叙事的空白。一直难忘除夕夜明公馆这一场戏。明镜独自坐着,望着空荡的屋子,想起三个弟弟都未归家,眼底满是落寞。忽听院外传来清脆的放炮声,她起身出门,见明楼、明诚回来了,眼眶湿润,笑着嗔怪两人孩子气。正说笑时,明台意外回来了,一向最疼明台的明镜更是惊喜,“姐姐只要见到你呀,什么烦心事都没了”。最受宠的明台是大家的开心果,他总是像小孩享受着大家的宠爱,撒娇、耍赖,哥哥姐姐都放任着他,在这乱世里护住明台自由烂漫的天性,是他们奋斗和守护的理由。也在此刻,“家国情怀”具象化地落地为“家庭守护”,明家姐弟守护国家,也是为了守护小家,为了让最爱的弟弟可以做个幸福的普通人。
残酷的是,明镜与明楼那么千方百计地想给明台一个平凡的人生,明台还是卷进来了。亲情既是他们最温暖的港湾,也是最脆弱的软肋,亲情与职责、家与国的冲突,赋予了传统谍战题材更为浓郁的情感冲击力。当明楼愤怒地质问王天风,为何要带走自己的弟弟,王天风反问道:“现在是战时,每天都在死人,你和我都可以死,唯独你兄弟不能死?”明楼所承受的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特工的职业风险,而是一种近乎残忍的伦理撕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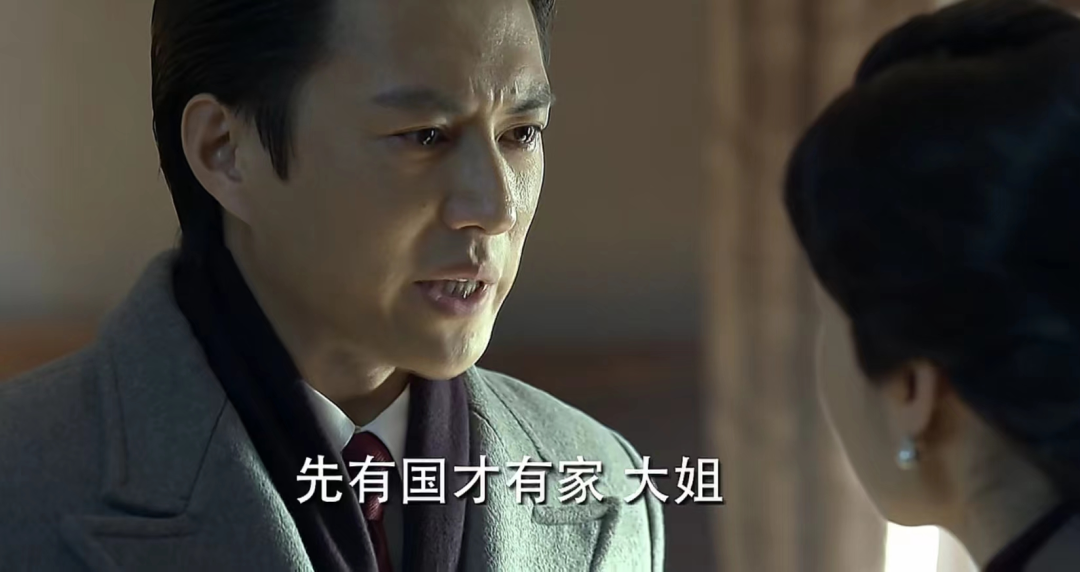
“谍战为骨、亲情为魂”才是《伪装者》最动人的部分,它既延续了传统谍战剧中身份博弈带来的紧张感和悬疑张力,更通过“家”这一情感核心,将人物的动机、痛苦与抉择具象化、人性化。明家姐弟都在家国大义与个人情感间挣扎的真实个体,他们的软肋与盔甲都源于同一个地方“家”,他们的爱、他们的痛、他们的牺牲,对于我们普通观众而言,更具共情力和感染力。
偶像非原罪,关键得用对
《伪装者》之后,刮起了一阵偶像谍战剧之风——由年轻偶像或演员担纲主演、凸显出年轻化、时尚化,但在这十年间,却没有任何一部谍战剧达到《伪装者》的口碑与热度,多数偶像谍战剧均以口碑惨淡而告终。比如陈学冬的《解密》(豆瓣5.2)、陈晓的《红蔷薇》(豆瓣6.8)、秦俊杰的《天衣无缝》(豆瓣6.1)、张若昀的《谍战深海之惊蛰》(豆瓣6.2)、任嘉伦主演的《秋蝉》(豆瓣5.7)、张一山的《局中人》(豆瓣5.2)、宋轶的《蜂巢》(豆瓣4.3)、曾舜晞的《孤舟》(豆瓣5.2)、杨幂的《哈尔滨一九四四》(豆瓣5.9),等等。仅有《隐秘而伟大》(豆瓣7.9)、《叛逆者》(豆瓣7.7)、 《追风者》(豆瓣7.8)获得了还不错的评价。
为何模仿者众多,却难以超越?“偶像谍战剧”的创作思路出现了什么问题?
回到2015年这个时间节点,这一年内娱迎来了流量时代。2014年10月,从韩国男子组合EXO出道的鹿晗决定回国发展,他发布了一条“我回家了”的微博,凭借粉丝刷出的1316万条微博评论斩获“吉尼斯纪录”,反向引发很多不追星的公众追问“谁是鹿晗”,2015年粉丝再将评论刷至1亿条,二次打破纪录。粉丝的数据,制造了一个“顶流”。起初,公众对流量明星的态度以好奇为主,对他们的“数据奇观”产生兴趣,试着了解他们的作品,流量明星得以在业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占据市场主流。
所以,虽然此前没有演过戏,但2015-2016年,鹿晗接连有《重返20岁》《我是证人》《盗墓笔记》《长城》等主演的电影上映。2016年的福布斯中国名人榜,鹿晗以1.8亿的年收入位列第二,2017年该榜单,鹿晗以2.1亿元的年收入排第二……

这就是流量时代的核心逻辑:数据制造流量明星,流量明星制造惊人的利润。
“偶像”和“流量”对于影视创作的影响并不相同。比如我们说《伪装者》是偶像谍战剧,这里的偶像,借用的是“偶像剧”的概念,请来青春靓丽的演员来出演正剧,“会演戏”仍是对年轻演员的潜在要求。“流量”当然也是青春靓丽、粉丝众多的偶像了,但流量打破了对“演戏”的基本要求——不管明星是否具备基本的表演能力,只要自带流量、能引发话题,Ta就是出演一部剧的理由,演技要求完全让位于流量带来的商业预期。

由于流量明星能带来可见的数据,资本与平台对其趋之若鹜,当时影视项目有“PPT四大神兽”的说法,只要在PPT上标明“鹿晗、杨洋”等人的其中一个,即便剧本、制作班底未知,视频网站也会花费天价购剧。在那个可以数据注水的年代,流量加持的剧集轻松几十亿上百亿点击率,有一部顶流主演的古装剧点击量更是达到匪夷所思的400亿次。
这一大背景下,偶像谍战剧创作不免受到流量思维的影响。比如谍战剧《解密》的导演启用陈学冬当主演,他在采访中直言:“我们都有过担心,我都是用老演员的,我没有见过陈学冬,我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是我同意了。”是什么关键因素促使导演最后拍板?“他们说他有1700多万的粉丝,如果用了他,我们现在网络可以签到什么价格?我立马说签他,不会演戏我也会让他演戏!”
偶像化谍战剧,异化为“流量谍战剧”,成为披着谍战外衣的流量剧。从角色设定到剧情推进,都围绕着凸显流量明星展开;主角设定“完美化”,能力脱离现实逻辑;反派“弱智化”“工具化”,谍战剧失去了核心的智斗张力;爱情线篇幅的过载,严重挤压谍战的叙事空间;叙事线完全围绕主角的个人成长与情感展开,忽略群像塑造,失去了传统谍战剧的宏大感……即便个别流量型演员具备一定演技,在单薄的情节、仓促的制作和扭曲的创作目标之下,也难以发挥出真正的表现力。


业内外并非没有意识到流量主导创作的问题,2017年起,多起流量明星的负面事件集中爆发。2017年,《孤芳不自赏》陷入“抠图演出”丑闻,同一年,明星一部剧上亿、一个综艺数千万片酬的“天价片酬”引发公愤;2018年,明星的税务风波,给公众带来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2019年,央视报道曝光某顶流微博转发量过亿背后的数据造假产业链,新浪微博随即宣布将转发、评论显示上限设置为100万……流量变成一个中性词,甚至是贬义词,“流量+IP”再也不是万应灵药。
近年来,观众对作品质量的要求显著提高,市场也逐渐趋向理性,但“以流量为中心”的思维定式仍在部分制作方和平台中存续。某些项目依赖明星自带的话题与粉丝经济作为保障,作品围绕流量明星展开叙事,创作重心倾向于满足粉丝偏好而非艺术表达本身。很多粉丝还会通过“撕番”、投诉、抵制等方式向制作方施压,要求明确自家爱豆“绝对主角”的定位,甚至连群像叙事都拒绝。
因此,偶像不是“原罪”,有问题的是将流量凌驾于创作之上的逻辑。是否“用对”偶像/流量,就取决于流量究竟是服务于作品、为作品锦上添花,还是让作品服务于流量,成为流量的附属品。《叛逆者》《追风者》口碑尚可,前提是作品本身是完成度合格的谍战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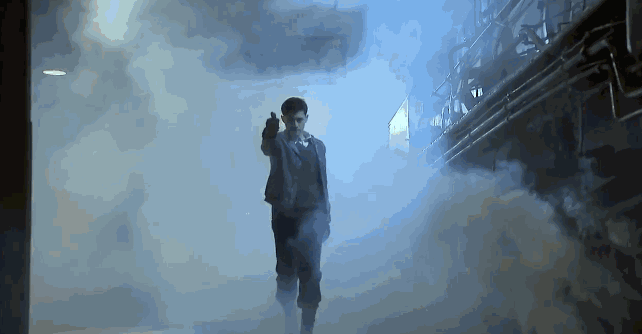
十年后的今天重温《伪装者》,也是在重申一种正确使用偶像的范式。尊重类型创作规律,让作品本身质量够硬,偶像的流量确实有助于作品的进一步出圈,实现真正的双赢。十年过去,《伪装者》依旧好看,但多少粉丝自嗨的流量谍战剧,早已湮没无闻。

排版:球球 / 审核:同同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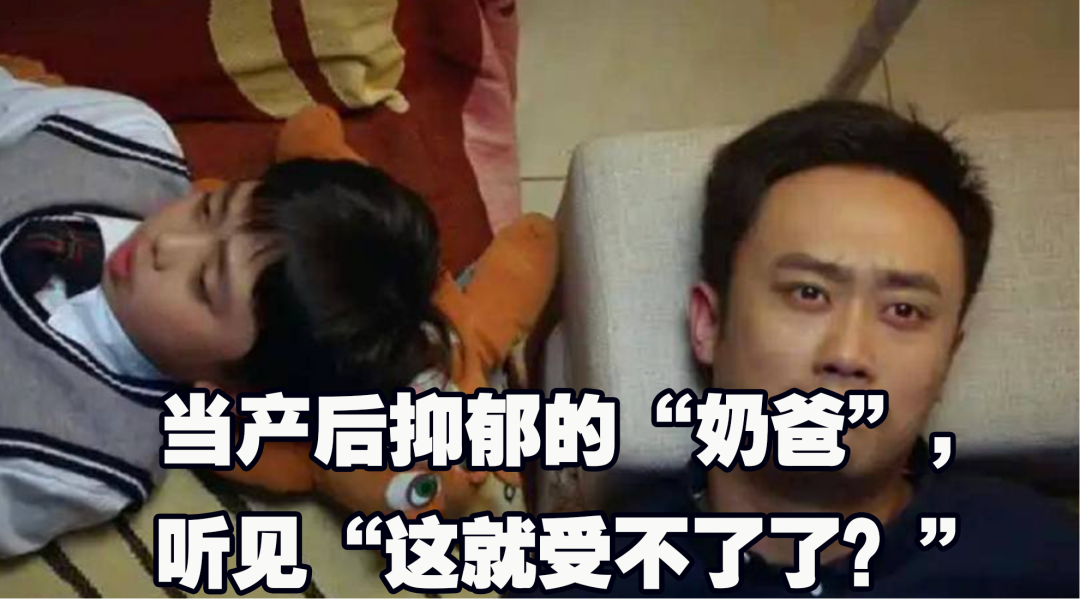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4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47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