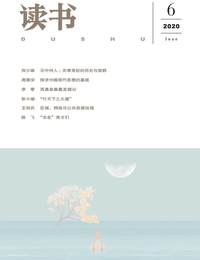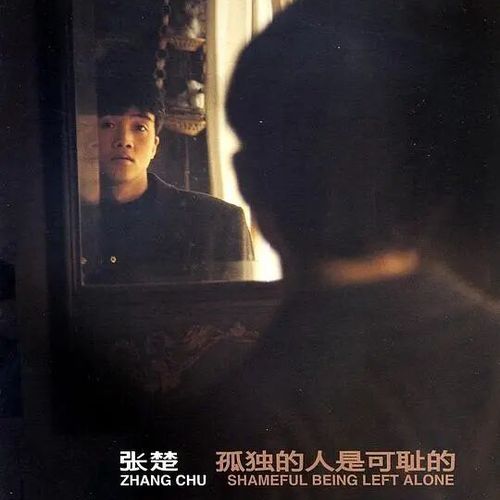探求中国现代思想的基底
作者:读书
2020-07-02·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934个字,产生4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周展安
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是在回应同时代危机的态势中展开的。这种危机以 “三千年未有 ”的强度刺激着中国现代思想的发育,迫使其必须跨出自身的知识脉络而关切到同时代的政治和社会议题。这一方面固然促使其在对现实的开放中保持思想活力,但另一方面又往往导致后来者以对象的政治光谱位置来把握思想的性质。由此,产生思想或进步、或落后的判断。而且,在这种判断中,“思想 ”是作为一种既成的规范形态而被把握的。但是,如果我们能穿透政治光谱而深入到思想的内容,尤其是,如果我们能进入思想者在获得定型化 “思想 ”成果之前粗粝的运思过程,能摸索到运思过程中的困惑与挣扎,那么就会发现以政治光谱为坐标来形成标签,对于 “思想”来说,是相当浅表化的。相比于可以用 “主义 ”话语来定型的 “思想 ”,思想者在运思过程中的艰苦更值得重视。可以说,越是艰苦的运思,越反映其对现实难题以及思想本身的忠诚。哪怕运思最终不能产出怎样成熟的思想成果,这种艰苦和忠诚本身自有其分量,既是对现实和思想全身心的感触和体认,也必然意味着思想的艰苦。尤其在晚清以来的现代思想世界中,危机前所未有的深重促使这深广与艰辛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状况。因此,对中国现代思想的研究就不能只停留在对各种成型 “思想 ”、成套观念的梳理上,不能只停留在对各种思潮论辩、竞逐之轨迹的追踪上,还应立体地考察思想的形成过程,考察思想者运思时的主体状态,从而去探求中国现代思想的基底。
坂元弘子教授的《中国近代思想的 “连锁 ”—以章太炎为中心》正可视为此种研究维度上的典范之作。此书不是历时性或者平面化地罗列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界诸多观念、潮流推移的历史,而是立体地剖析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李叔同等多位思想人物的运思过程与主体状态。而这些人物在主体状态上所表现出的极致性,尤其能够体现所谓对思想的忠诚和由此而来的思想的艰苦。这不是观念史,也不是知识史,而毋宁说是思想之生命史的写法。它摆脱了以政治力学来规范和回收思想脉动的路数,展现了思想自身的活力,尤其是思想不断向极限处开掘的立体纵深脉络,从而使我们经由这本书来探求中国现代思想之基底成为可能。
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是内外双重危机的产物。坂元弘子认为,对这双重危机的思想性把握,可以从 “个体与共同体 ”之关系的角度切入。在谭嗣同,这一课题具体表现为以 “以太 ”为基础的“心力 ”对“秦政荀学 ”之旧伦理和旧秩序的冲撞,并走向 “万物一体论 ”;在章太炎,表现为 “大独必群,群以独成 ”的群独关系以及对 “中华民国 ”之民族秩序的思考;在熊十力,表现为 “仁体 ”与“大同世界 ”的内在沟通;在梁漱溟,表现为 “生命 ”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的“团体生活 ”之间的联系。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的确可以说构成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思想的地平。严复通过对穆勒《群己权界论》的翻译而展开的对于 “群”和“群己关系 ”的思考、梁启超对于私德与公德之关系的思考以及现代史上更常见的个人与国家、社会、阶级之关系的讨论,都可以纳入这一课题。但和严复等更多注重 “群”与“己”,或者 “个人 ”与“国家 ”的对立关系从而划定各自的边界相反,坂元弘子笔下诸位思想人物的思考更倾向于 “个体 ”与“共同体 ”之间的联系与沟通。这两者之间的纠缠构成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20777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