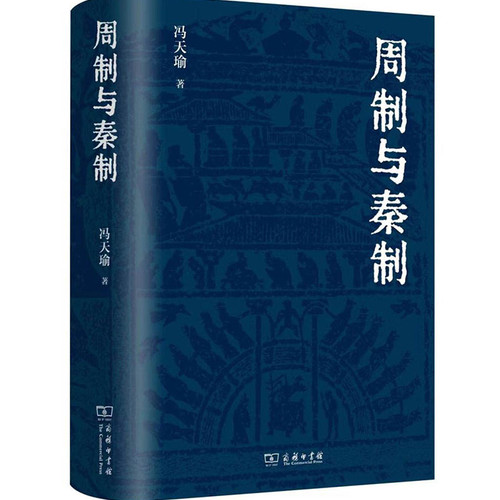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山中”
作者:维舟
2020-08-19·阅读时长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2436个字,产生5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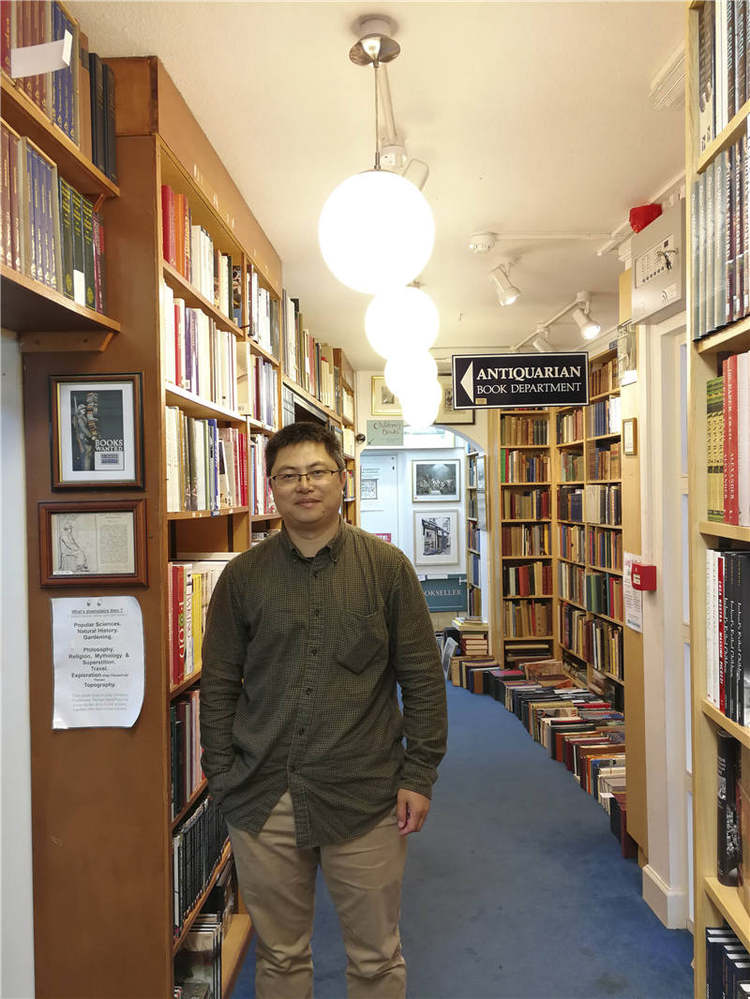
魏斌
江南也有了名山
世人常说“黑暗的中世纪”,但中世纪的人未必自视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不仅如此,种种现代制度、理念和技术,其实正是在那时所孕育的。由此反观中国,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后那长达400年的时间,也多被看作是分裂、悲惨和倒退的年代,但事实上很多新事物也是在此时涌现的:科举制的前身“九品官人法”渐趋完善;佛教和道教的成熟化;文学、史学、书法和绘画的独立发展;当然,还有“山水”“风景”和中国式园林的成形。
如何理解这些变化,那时的“山中”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可以说,那是一个“发现山中”的时代。一方面,长期持续的战乱和政治的污浊,使很多人选择逃入山林,或构筑坞壁以自保,或隐居修行以自高,《桃花源记》就是这一时代精神的表征;另一方面,自东吴征讨山越起,历朝为了在攸关生死存亡的战争中立足,都不断深入边荒,搜山料民,对驯服这些“负固山险”不服“王化”者的国家意志从未如此强烈。与此同时,方士、逸民、隐士这类远离尘世的文化性山居者,又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随着4世纪以后佛教山寺的兴起和山中修道的宫观化,山岳的文化景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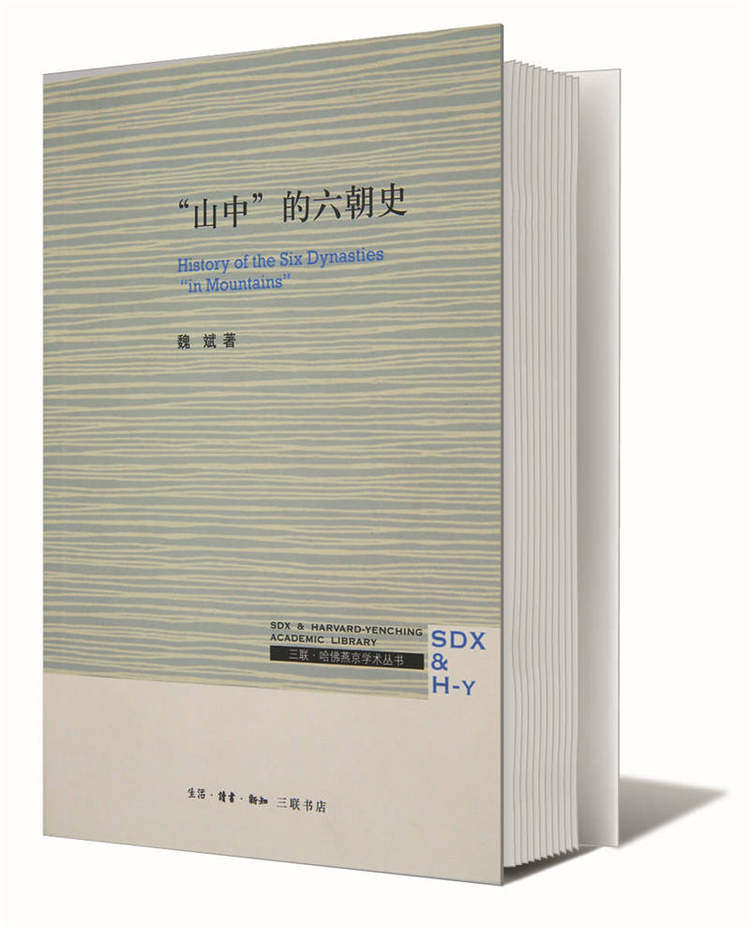
《“山中”的六朝史》
在此可以借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观点:如果围绕着某个静止空间形成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那么前者将在人们的互动中充当至关重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枢纽。虽然他用以阐释的主要是城市里的建筑物和公共空间,但六朝时的“山中”也完全可以说是这样一个“意义枢纽”,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魏斌在《“山中”的六朝史》中所言,它作为观察历史进程的窗口,“呈现着六朝历史的各种要素:正统与边缘、士庶与寒人、侨民与旧民、都城与地方、信仰与生活、知识与身份等等”,在此,历史具有了强烈的空间性,也更能让我们体会和想象当时普通生命在一个丰富交错的场景中“活着”的状态。
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其首要的特征是:它乍看是远离“尘世”的,似乎更多的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其实却是“文化”的。实际上,单纯的“自然”是没有历史的,有也是属于自然史、地质史的范畴,而本书所说的“山中”所包含的,乃是包括祭祀、寺院、道馆、学馆、隐舍等在内的文化信仰系统,是被人的文化活动所界定的“山中”。更进一步说,也正是文化内涵决定着这些名山的声望和价值,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像普陀山、紫金山、清源山这些名山,都不过数百米高,它们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正是一代代的文化实践所沉淀下来的。
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山林一直是圣域。《礼记·祭法》说得明白:“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这也是五岳、国山等山岳信仰的社会心理基底:人们相信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福祉有赖于山岳保障。对立国于南方的六朝来说,这很自然带来一种政治焦虑:除南岳之外的四岳都在已沦陷的北方,那么如何论证本朝的合法性?对道教等宗教团体而言,也有同样的挑战:如何在一个原先相对陌生的南方安顿自己的精神信仰?
从本书分析的东吴国山禅礼事件、“神仙南渡”和江南名山的兴起来看,答案是很明确的:六朝历史的一个脉络便是政治文化的“在地化”,表现为对南方地域认同的强化,这也与北方流民与土著逐步融合、最终“土断”为本地居民的趋势一致。原本在中原视野中被边缘化的江南地区,也有了自己的“名山”,而“土地所在”的小山也开始被列入朝廷祭祀。在当时南北分裂的背景下,这不无与北方抗衡、争正统的意味,但就整个中国史的大局来看,却又意味着中国文化因子在南方的不断深入、扩散,最终将原本处于文化视野之外的“蛮荒”都纳入了这一扩张的文化网络之中,为之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文章作者


维舟
发表文章33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420人
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