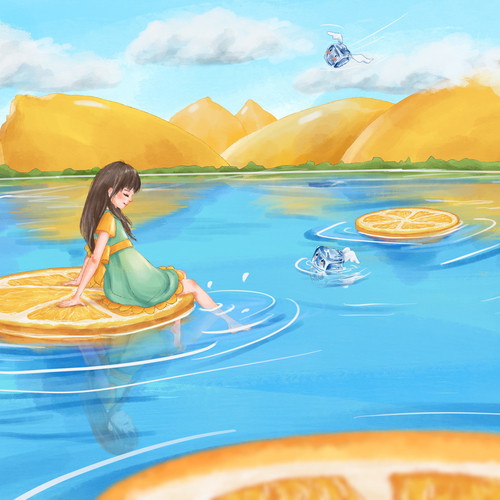《末代帝王君》(第四章)
作者:余味
2017-09-27·阅读时长14分钟
第四章 师心可鉴
时间转瞬即逝,不知不觉间翁同龢已经教授了我一月有余。这一个多月以来翁同龢倾心相教,一开始我对他抱有极大的偏见因而听课极不专心,但未过多久我便被其丰厚学识所吸引,便逐渐静下心来听其讲授。此后我虽然偶尔读书走神但总体来说对于学业还算比较尽心,因而学问上有了较大的长进。一开始我对翁同龢的确抱有偏见,因而不愿意承认其大儒身份,认为其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但随着一个多月的相处,我发现他对于古文经典的掌握程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孔孟程朱的话他张口就可以引来,解释经学古训时他不用参考注解便信口而出,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一个时辰,显然他对此早已熟记于心。有时候我故意拿出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前去询问,他也总能引经据典对答如流,每次都让我惊讶感叹不已。
我不得不承认翁同龢的确是当代的大儒,我们虽然只相处了一个多月,但他那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问已经让我折服。他对于汉文经典的诠释和讲解可谓是深入浅出,让我大为受益,伊克哈这个糟老头与之相比真是相形见绌,二人真是有天壤之别。然而使我感触最深的倒不是他们二人在学问上的差异,而是他们在品德上的区别。伊克哈品格低劣,经常趁着入宫教辅我的机会偷拿宫里的东西,像什么犀牛角杯、沉香手串、白玉扳指等都曾被他偷过,就连养心殿里的熏香炉也曾被他偷了出去变卖钱财。不仅如此,伊克哈还经常仗着自己的帝师身份向别人索取贿赂,其卑劣行径真是让人不齿。与之相比,翁同龢实在好得太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翁同龢的好感愈发增加,对他的不满之情日益降低,朱维国更是对其毕恭毕敬,完全以师礼而相待。其实,朱维国是个严格恪守礼法的人,他一开始对于伊克哈他也颇为恭敬,只是后来看到伊克哈寡陋无知品格低劣的种种迹象才逐渐减少对其的尊敬,直至后来他和我一样打心眼里鄙视伊克哈这个家伙。现在对于翁同龢,朱维国是打心眼里敬佩,因而对他的礼数都很周到。我虽然对于翁同龢愈发欣赏,但还没有达到崇拜的地步,毕竟与其初次相见不快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所以并没有完全被他所征服——直到他诚心护主这件事的发生。
这日上完早朝后皇太后特意将翁同龢留了下来,等到其他朝臣全都已散去,皇太后当着我的面问他道:“翁先生,算起来你给皇帝授课也已经一月有余,对于皇帝的表现还满意吗?”皇太后一直称翁同龢为翁先生,而不是直接称他的名字或官衔,这是对于他额外的尊重,一般的大臣绝对受不到这样的礼遇。翁同龢看都没有看我,说道:“皇上天资聪颖,这对于读书自是好事,只可惜皇上根基较浅,对于经书典籍所读不多。此外,皇上习文听课也时时分心走神,长此下去恐怕难有大的成就。”好你个翁同龢,竟然敢当着我的面向皇太后嚼舌根!他这一番话顿时将我一个多月来对他累积的好感减了一半,趁着皇太后还没发话,我先是驳斥道:“翁先生是以培养鸿儒的标准来要求朕,可朕并想不作名儒学者,而是要作执掌朝政的皇帝,所以朕更多需要学习的是治国之道,而不是古圣先贤的典籍。”翁同龢说道:“皇上此言差矣!古圣先贤的典籍中就蕴含着治国之道,不精读这些典籍又怎领会治国之道呢?”我驳斥道:“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出身草莽,他们大字都不识几个,古书典籍自是没有读过多少,可他们却开创了大汉和大明两个盛世王朝,难道他们不懂治国之道吗?”
皇太后训斥我道:“皇帝,你怎么能用这种语气和自己的师傅说话呢?尊师的祖训难不成你忘了?”我不满地答道:“儿臣和翁先生有言在先,在毓庆宫中他是师傅儿臣是学生,在朝堂上儿臣是皇帝他是臣子,此刻是在朝堂上,所以…”“所以你就不用尊敬师傅了?”皇太后冷声问道。我的确和翁同龢有这样的约定,但是面对皇太后咄咄逼人的态势我却说不出话来,又听到皇太后接口说道:“尊师是每个学生所必须恪守的准则,咱们帝王之家更是要在这方面做出表率,你如此顶撞自己的师傅,又怎能做出表率?还不快向翁先生赔罪!”我虽然极不情愿,但是惧于皇太后的淫威也不得不低头认错,但我还未开口致歉翁同龢就率先开口道:“皇太后,微臣确实和皇上有约在先,此刻在朝堂上微臣是臣而皇上是君,世上哪有君向臣赔罪的道理呢?”皇太后却坚持说道:“尊师向来不分场合,不管是在哪,你都是师傅,他都是学生,这点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只要皇帝还认你这个师傅,那他就必须时刻尊敬你,眼下他顶撞你便是无礼,所以他必须要向你赔罪,翁先生,你不必推辞。”我知道皇太后心意已定,只好低头向翁同龢认错赔罪,他倒也没有难为我,接受了我的赔罪。
我是怀着极不情愿的心情向翁同龢赔罪认错的,所以内心里对他颇有些反感。因为如此,回到养心殿里我就一直闷闷不乐,清月见此便问道:“怎么了皇上?自从下朝回来后我就看您不大高兴,到底是谁惹到您了?”我把拳头紧握向桌子上一砸,然后愤恨地说道:“除了他还能有谁?”清月巧妙地解开了我紧握我的拳头,然后说道:“皇上您先消消气,犯不着如此动怒,以免伤了您的身子。”随即她又说道:“李总管有皇太后作靠山难免有些骄纵,倘若他因此说了什么过分的话,皇上不去与他计较便是,何必因此而动怒呢?”我说道:“李莲英的确骄纵无礼,朕也打心眼里厌恶他,但这次的事情与他无关。”清月随即又便道:“老佛爷是尊者长者,她对您的关心和垂爱有目共睹。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您是大清的皇帝,她对您一定给予了极大厚望,因而难免会责备您几句,您也不必为此在意。”我摇头说道:“朕也不是生皇太后的气。”清月又说道:“朝中的大臣敢于直谏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越是刺耳的话就越可能是发自肺腑,只有忠臣才敢不畏威严直言上谏,皇上因该为此高兴才是。”我说道:“朕也不是因为大臣直谏而生气。”清月颇有些诧异,便问道:“那到底是谁惹到您了?您总得说出来吧。”
我说道:“就是那个惹人生厌的老家伙。”清月又问道:“哪个老人竟惹得您如此动怒?”我说道:“他自恃才华卓越,竟然目无人君,实在是惹人生恨。哼!这样的人有什么了不起?得过状元能怎样?当了帝师又如何?”清月笑道:“原来皇上是和翁同龢生气,他怎么也算是您的老师,您也不必如此贬斥他吧!”我说道:“他竟然说朕读书少根基浅且听课不专心,还说长此以往朕将难有大的成就。他当着朕的面就敢如此讲,你说可恨不可恨?”清月说道:“若是翁同龢真是当着皇上的面如此讲,那么奴婢倒是佩服他的人品,因为这恰恰说明他是一个敢于在人前直言的君子,而不是一个在人背后乱嚼舌根的小人。皇上应该为此高兴才是。”我不悦地说道:“清月,你是朕的侍女,怎么不帮着朕说话,反倒是处处袒护翁同龢呢?”清月笑道:“奴婢是帮理不帮人,皇上若是说得有理奴婢自会向着皇上。”我对此未加理会,继续说道:“朕要翁同龢传授治国之道,可他却偏偏只讲授古圣先贤的典籍,竟然还说治国之道蕴含在其中,这分明就是与朕作对。”缓了口气我接着说道:“那些古圣先贤的典籍佶屈聱牙,全都是些晦涩艰难的文字,这样的书籍读再多于治国又有何用?”
清月说道:“读书的事奴婢懂得不多,可是翁同龢能够在众多学子中脱颖而出成为状元,这足以证明其非凡的才学。此外,翁同龢能够担任同治帝的老师达十余年而不被罢黜,这足以体现其卓越才干。翁同龢完全可以胜任帝师之职,他如此教导皇上必有道理,皇上却为何不信任他呢?”我说道:“朕初次与翁同龢见面彼此就颇有些不快,所以朕怀疑翁同龢想借机报复朕,他向皇太后控诉朕可能便是源于此。”清月说道:“皇上是一国之君,怎么度量如此狭小?翁同龢是当世鸿儒,皇上岂可将他视为小人?有一件事恐怕皇上还不知道,奴婢可以说给皇上听听。”我说道:“好,你直说吧。”清月说道:“老佛爷的侍女巧儿和奴婢私交甚好,前两日翁同龢到长春宫与老佛爷谈论政事,巧儿当时就侯立在老佛爷的一旁。讨论完政事老佛爷就说道:‘皇帝年幼尚不能理政,还望翁先生多方教导,以使皇帝成才。’翁同龢答道:‘臣身为帝师,理应尽教辅之责,帮助皇上成才更是臣分内之事。’老佛爷说道:‘伊克哈临走时说皇帝轻慢而不尊师,贪玩儿不好学,长此以往恐难有所成。如此说来教辅皇帝实在是一件难事,现如今我将这副重担托付于你,实在是难为你了。’”
听了之后,我大为不悦,禁不住在心里骂道:“好你个伊克哈,你自己学问不足无力教辅竟还反过来倒打我一耙,临走之时竟然还要诋毁我一番。伊克哈啊伊克哈,你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清月接着说道:“翁同龢听罢摇了摇头,说道:‘伊克哈大人此言差矣!以臣愚见,皇上天资绝非泛泛之辈,其读书之用功也非常人可比,老臣略加教辅一番皇上必可成大器。’”我难以相信翁同龢竟会如此说,所以便问道:“他当真是如此说的?”清月肯定地说道:“这还能有假?难道皇上连奴婢也不信任了吗?”我点头表示相信,清月接着说道:“老佛爷问道:‘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和皇帝相处的时日不多,怎么就敢如此断言呢?’翁同龢答道:‘话虽如此,可事实却未必尽然。皇上的史书典籍虽然读得不多,但是他敏而好学的态度却诚为可贵。老臣昨日去教辅皇上,看到皇上的书桌上放满着治国理政的书籍,老臣打开一看里面尽是皇上写下的批注,皇上的好学由此可见。试问如此好学之人焉能不成气候?’”
我之前还疑心清月是否想为翁同龢开脱而编造谎言,如今看来清月所说不假,因为我在毓庆宫书桌上摆满写批注的书之事清月并不知晓。又听到清月说道:“老佛爷听到此问道:‘那依你看,当今皇帝和同治帝孰优孰劣?’翁同龢答道:‘同治帝是贤者,当今圣上亦是贤者。’老佛爷不肯就此止步,便继续问道:‘那么他们二人谁更贤能呢?’翁同龢有些踌躇,老佛爷见此说道:‘你只需如实而言便可,不必有所顾忌。’翁同龢说道:‘同治帝贤而刚毅,当今圣上贤而聪慧,二者各有所长,都是难得的人物。’老佛爷听罢便指着翁同龢说道:‘翁常熟,你可真是个老滑头。不行,今日你非得给我个确切的回答。’翁同龢便不加思索地说道:‘既如此,那老臣就斗胆放言。以臣愚见,似乎当今圣上更为贤明。’老佛爷问道:‘你此话当真?’翁同龢答道:‘老臣亲自教辅同治帝和当今圣上,他们二人的才学品德和悟性老臣颇为了解,依老臣来看,当今圣上更为贤明。’”
我听后说道:“既如此,那翁同龢又何必当着朕的面批驳朕呢?这样做未免太过愚蠢,而且也说不大通。”清月笑道:“翁同龢是当世奇才,说话做事又怎么会和寻常人一样呢?皇上如此揣测他,这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抢上前去胳肢清月,口里喊道:“你竟然敢嘲笑朕,朕准饶不了你。”清月痒得不住发笑,口里说道:“好皇上,饶了奴婢吧!”我问道:“那你还敢如此嘲笑朕么?”清月答道:“不敢,再也不敢了。”我这时止住了手,清月才恢复了过来。因为刚才胳肢的动静颇大,清月的衣服稍有些解开,此时他和我同时注意到了这点,我是有些愧疚,她是有些脸红,我们两人彼此都有些尴尬,好在此刻的景象没有被他人看见。清月整理好衣服后便走了出去,我还在思索她刚才所讲的话。
我之前看书上有这样一个故事:“晋朝重臣王敦起兵作乱,他的弟弟王导便跪在宫殿门口请罪,这时恰好周顗进宫,王导便请周顗替自己求情,周顗没有搭理他便走进宫去了,然而周顗进宫却为王导说尽了好话,百般替王导辩解。周顗出宫时王导还跪在门口,王导向周顗打招呼但周顗却仍旧没有搭理他,非但如此,周顗嘴里喊着‘今年杀死乱臣贼子,换个斗大金印带在身上。’但是周顗回去后就写了一篇奏则替王导求情,然而王导不知实情,认为周顗见死不救,因而十分记恨周顗。后来王敦掌握了朝政,便要将周顗置于死地,王导也未加劝阻,默认了这一做法。直到王导整理中书省文件时才发现周顗极力为自己辩白的奏折,然而此时周顗已经被杀,想到此处王导悲叹道:‘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如此说来,翁同龢倒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他敢于把难听的话当面说出来而不再人背后嚼舌根,这倒也配得上帝师之职。自此以后我又恢复了对翁同龢的赞赏之情。
不久后发生的一幕场景更让我对翁同龢肃然起敬。那是在某日早晨授读完以后,我和他一同在院落里散步,突然墙角上的一只猫发疯一般地从墙上向我扑来。我当时凝神交谈并未留心于此,翁同龢见状立即扑在前面护住了我,结果他自己的脸让这个猫抓的伤痕累累,最终鲜血布满了整个面颊。我赶忙召集御医为他诊治,所幸只是些皮肉伤并无大碍,但这件事使我对翁同龢产生了敬意。口头上喊着忠君爱君的自有不少人,然而敢于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依然保护君主的人实在是少数,翁同龢恰在这少数人之列。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翁同龢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臣,而非驰骋疆场的武将,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更是让我大为感动。我以前只是将翁同龢视为一个儒臣罢了,尽管他满腹经纶但毕竟不是一个干将,如今亲眼目睹他做出这惊人的一幕我大为赞叹。在某些时候儒臣的勇猛刚毅甚至要超越武将,眼下的情况便足以证明。
御医为翁同龢上了药,之后翁同龢就回家修养,因为伤及了脸部不便见人,所以他只得闭门不出,同时中断了早朝和授课。当天晚上我便前往翁同龢的府邸探望他,进入府邸后我嘱咐管家道:“不要惊扰翁师傅,也不必让他前来迎驾,朕只进去看看他就好。”在管家的陪同下我走到了翁同龢的卧房门口,我对着管家说道:“你且下去吧,朕想一个人和翁师傅谈谈。”管家应声而去,我迈着步子走进了卧房,翁同龢问道:“是谁啊?”我答道:“翁师傅,是朕来看你了。”翁同龢此时正在拿笔写着什么,见我来了他便立即放下手中的东西,然后准备起身,我忙说道:“此刻只有咱们二人相见,翁师傅不必行礼。”翁同龢说道:“这怎么行呢?如今又不是在毓庆宫,老臣怎么能不守人臣之礼呢?”他坚持行完了大礼,然后恭敬地立在一旁。我见此说道:“翁师傅有伤在身,还是赶快上床躺着吧。”翁同龢说道:“皇上在此站着,老臣若是安然躺在床上,岂不是君前失礼吗?”我说道:“翁师傅,朕今日是来探望你的,探望的目的是为了你早日康复,如今你因为朕的到来而不卧床休息,若是因此而延误了病情,那么这可是朕的罪责啊!”翁同龢见此才上床躺下。
我问道:“翁师傅的伤可有好转?”翁同龢答道:“多谢皇上关心,伤口较日间已好了不少,只有如今脸上还略微有些疼痛。”我问道:“你今日向前直扑时可曾想到了眼下的疼痛?”翁同龢说道:“微臣当时心无所想,只知道保护皇上,所以断然没想到这点。”我又问道:“你若是想到了这点,那你还会奋然不顾地向前直扑吗?”翁同龢不加思索地说道:“当然,为了保护皇上老臣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也在所不惜。”我握着翁同龢的双手说道:“翁师傅待朕一片真心,一想到之前轻侮戏谑翁师傅朕就深感愧疚,还望翁师傅不要对朕之前的无礼举动介意。”翁同龢说道:“皇上说的是哪里话?之前的种种事端都已过去,皇上当时也是无心为之,老臣何苦为此而耿耿于怀呢?”我说道:“翁师傅果然深明大义,朕对此真是佩服不已。”翁同龢说道:“皇上谬赞了,老臣这点修行与品德哪里值得提倡呢?”
我又看到了床旁边的桌子上放着笔和本,想起了刚才翁同龢书写的样子,便问道:“这是翁师傅写的什么大作啊?可否让朕拜读一番?”翁同龢说道:“这不过是老臣的日记而已,真是再寻常不过,实在不值得皇上一看。”我说道:“翁师傅的才学是当世一流,想必行文习作也是精妙绝伦,朕早就想一睹翁师傅的文笔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如今难得有此良机,翁师傅又何必推辞呢?”翁同龢知道再说下去只会显得自己狭隘而吝惜日记,便说道:“那皇上就拿来看吧,只要你不嫌弃就好。”日记不同于公文,它更加私密,自然也更容易表达出写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我也急于窥探翁同龢的内心世界,所以便迫不及待地拿起日记去看。首先映入我面前的是今日刚写的日记,只见写道:
“约巳时一刻,与上并行,一猫骤然疾驰而至,其爪甚锋,其齿甚利,其态甚獠,其桀骜之性尽显。予见之颇有惊色,上尤浑然不觉,予不忍惊扫上之雅致,亦不忍秽体污及龙身,更不忍贱畜伤及贵体,遂率身而阻之,后予面有所破,鲜血横流,然上终毫发无伤,幸哉幸哉!忠臣卫其君,仁师护其徒,此天地之义也!予位列朝臣,又忝为帝师,竭力卫上乃予分内之责,故今日…”
我看后又是惊讶又是感动,翁同龢待我的一片忠心由此看见,看来清月所说当真不假。我望着翁同龢满目深情地说道:“翁师傅待朕如此之厚,朕待翁师傅如此之薄,思来都是朕心胸太过狭隘,竟然将翁师傅错认为歹人小人,这一切都是朕的罪过。”翁同龢说道:“皇上言重了。初次相见时皇上对老臣确有不恭之处,但后来皇上对老臣愈发敬重,今日皇上对老臣全是以礼相待,又怎么能说待老臣薄呢?”我点了点头,然后继续看日记,只见有一篇这样写道:
“今日教辅已毕,上之勤恳好学实属罕见,其书法习字亦颇为可观,其应时习作更非泛泛,比之穆宗,上实尤过之。然上之心性过急,唯求治国之道而欲废先贤典籍,此诚为谬也!古之旷世明君皆先通典籍而后治天下,先贤典籍尽含治国良策,典籍不通则难以治国,今上欲废典籍而求治国之道,此尤南辕北辙,必不得也!自今以后,予必苛之察之,使上有所悟也!”
我又说道:“原来翁师傅批驳朕的缘由便在于此,朕之前不了解翁师傅的良苦用心所以才对你以言顶撞,如今思来真是后悔。翁师傅放心,朕今后必当用功学习古圣先贤的典籍,力求通晓古今帝王的治国之道,以期成为一代明君。”翁同龢抚着胡子说道:“若能如此,老臣就是死也心安了。”我说道:“翁师傅先好好养病,唯有你身体好了才能给朕讲解古圣先贤的典籍。朕今日就此别过,改日再来探望你。”翁同龢想要起身送我,但我及时止住了他,然后便独自一人走了出去。
文章作者


余味
发表文章16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43人
积极向上……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