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意义,或许是人类最特殊的执念
作者:张宇琦
2021-04-07·阅读时长16分钟

“认知神经科学家,研究无聊,还是摆脱不了无聊,即使手里抱着吉他。”在社交网站的个人主页上,詹姆斯·丹克特(James Danckert)博士用自嘲的口吻透露出他最热爱的几件事。今年49岁的丹克特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心理学系教授,他主持着一个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是“无聊研究”领域最活跃的学者之一。但在31年前,身为墨尔本大学新生的丹克特从未设想过这些头衔,他打算读英语文学专业,然后成为一个有名的小说家。但在大一结束前,因为哥哥在车祸中受了脑外伤,丹克特开始对人类最复杂的器官——大脑着迷。
2020年6月,丹克特的第一本书出版了,不是小说,而是他与英国约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约翰·伊斯特伍德(John D. Eastwood)合写的《无聊透顶:无聊心理学》(Out of My Skull:The Psychology of Boredom)。这本科普读物的标题不一定有助于销售,但书的内容看起来极富现实意义——疫情下的隔离生活一眼看不到尽头,人们都在为如何消磨时间犯愁。
但两位作者的初衷并不止于一本应景的自助书。他们在写作中引用了超过400篇文献,除了横跨心理学各个分支的学术论文,哲学家叔本华、祁克果,诗人布罗茨基,艺术家沃霍尔等不同时代的思想者关于“无聊”的论述,也被囊括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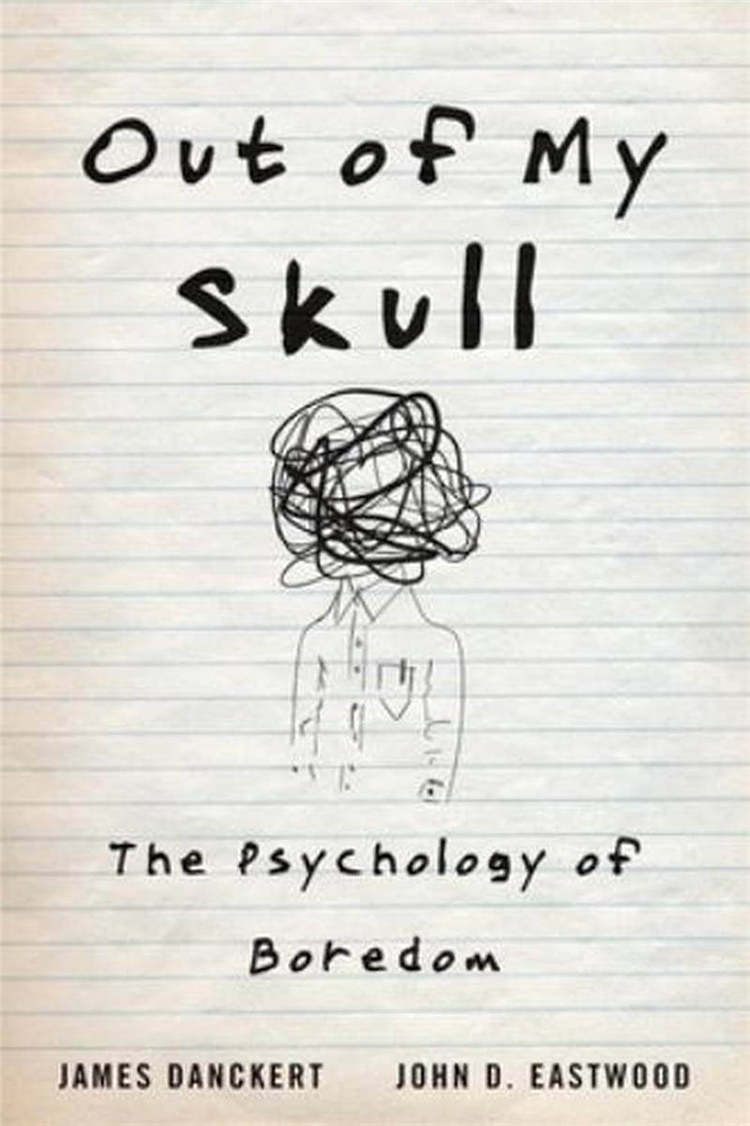
无聊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可能有严重后果的负面感受。但《无聊透顶》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明,当无聊出现时,正是我们正视自己的欲望、展开新行动的契机。
在我们约定的视频访谈的开始,我对丹克特说:“祝贺你们完成了一个让科学发现和人文思想自由对话的叙述。”丹克特微笑着回应:“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说过一句话,我很有共鸣:‘科学和文学不是两个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身后的墙上,挂了两把漂亮的吉他。
心理学家们如何探究无聊的本质?当我们感到无聊时,身体会出现什么变化?现代人是不是更容易无聊了?在丹克特的回答中,我们也许能够收获一种看待生活的新眼光。
寻找一种普遍的“无聊”
三联生活周刊:在《无聊透顶》的序言中写道,“无聊”是一个普遍存在但难以捉摸的概念。研究任何较为主观的人类体验可能都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研究“无聊”的困难之处?
詹姆斯·丹克特:我们可以先回想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一句话。詹姆斯对于人类境况有非凡的洞察。在关于注意力的论述中,詹姆斯曾写道,“每个人都知道注意力是什么”,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它真正的意思是,每个人对注意力都有一种出于直觉的理解。类似地,当你问朋友和家人,你觉得无聊是什么,人人都可以给你一个答案,但每个人说的又必然有所不同。这大概是研究者在试图理解无聊时面临的基本挑战。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可以这样区分,科学家一般将无聊作为生理现象还是心理现象进行研究?
詹姆斯·丹克特:大部分研究者把无聊作为一种自我报告的主观现象处理。我们把参与者带进实验室,问他们上个月、上一周以及当下感觉如何,并请他们完成各种任务。从这个角度讲,目前的研究大多采取了探究认知、情感现象的方式。神经影像学和生理学的研究相对较少,还处在发展的初期。
我认为无聊研究不是一个特定的子领域,它跨越了不同领域的界限。情感、注意力、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甚至跨文化——比如,人们在中国和美国体验的无聊是相同的吗?这些都是心理学家探索无聊的维度。无聊研究也横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有不少研究者致力于理解人们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中体验的无聊,他们的结论可能直接影响政策和制度的设计。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作为一个认知神经科学家,你最初是如何对“无聊”产生兴趣的?为什么相信它值得研究?
詹姆斯·丹克特:对于我来说,个人生活和科研经历的影响都有。在我19岁时,我的哥哥出了场车祸,受了相当严重的脑损伤。虽然他最终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也能继续工作,但在康复期间,他经常说他对很多事感到无聊。而在受伤之前,那些事并不至于造成困扰。很明显,频繁感到无聊让他的生活更艰难了,无聊不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而那时我正在大学接受临床神经心理学的训练,这个学科关心的正是脑损伤病人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帮助他们回归从前的生活。参与一项研究时,我负责评估了大概20个病人,其中大部分是和我哥哥一样有类似脑损伤的年轻人。于是我借机问了他们所有人一个问题:相比受伤前,你感觉更无聊了吗?相当一部分人都回答,是的。不仅如此,这个问题还让他们很激动,因为几乎没人注意过他们的生活发生了这个重要的变化。当然,这些只是源于个人经验的轶事,还不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结论。当时有几篇神经科学论文提到脑外伤病人报告无聊的事,但都只是作为一种不太重要的趣闻去谈论,还没有人进行测量。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无聊的本质,心理学家在何种程度上已经达成共识?
詹姆斯·丹克特:可以说,过去三四十年中,无聊研究者一直在努力明确无聊意味着什么。整个90年代,也就是无聊研究的起步阶段,我们基本是在探究无聊通常与什么联系在一起。我想,是在最近的10年中,我们才开始真正定义这个状态本身。目前很多心理学家都认同,无聊是一种对行动的召唤(call to action),是一种功能性的状态。换句话说,无聊是一个信使,他的出现告诉我们,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发挥你的认知能力,你需要去做些别的。
但关于无聊的性质的讨论远未尘埃落定。一个重要问题是,只存在一种无聊,还是很多种?在去年新发表的文章中,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的哲学教授安德里亚斯·埃尔皮多鲁(Andreas Elpidorou)很有力地论述了,无聊的本质是单一的。我现在也倾向于这种观点。但在研究无聊的早期,我曾认为无聊可以被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焦躁型和冷淡型。这个界定源于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拉尔夫·格林森(Ralph Greenson)的个案分析,他在一个病人身上看到了这两种近乎对立的形式。但现在我认为不存在冷淡型无聊这回事。当你处于情感冷淡(apathy)状态,你没有兴趣做任何事,想象你长时间窝在沙发里看电视节目,但感觉不到这个状态有什么值得改变的,直到平静睡着。可是无聊不是这样的,无聊是一种受到驱动的状态,你一定是想做些其他事,但你一时没找到满意的选择。我想,我们现在已经更加趋近无聊的真相,但讨论还在继续。
“无聊”的发生机制
三联生活周刊:在《无聊透顶》中写道,造成无聊的既有外部因素,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关键是人的需求与外部所提供的条件出现了某种错位。关于无聊是如何发生的,是否已经相当明确了?
詹姆斯·丹克特:虽然我们仍在试图确定无聊是单一的还是多种的心理状态,但无可辩驳的是,导致无聊的前因是多重的,被研究得最多的有三个。
首先是单调,也就是缺乏变化、多样性。早在19世纪末,工业组织心理学家雨果·明斯特博格(Hugo Münsterberg)就关注到了工作场所中的单调问题,那时人们的工作性质正在发生转变,从相对危险的重体力活更多变成不费力但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比如在工厂流水线上挑出质量有问题的零件。行动受限,被强迫做某件事,也是一个与单调经常同时出现、相互加强的因素。
第二是意义的缺失。单是重复某个动作不一定无聊,无聊的人一定是看不到这个动作本身的任何价值。所以,即使不享受工作本身,流水线工人可能不至于感到无聊透顶,因为赚钱供养家人对许多人是一个强大的意义来源。
第三,当你无法集中注意力,通常就要感到无聊。比方说,很多人需要与电子表格打交道,但长时间录入数据会让人烦躁、犯困,这些都是注意力下降,需要提高大脑兴奋水平的信号。打个盹或者上上网,可能就会得到缓解。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能这样理解,在感觉无聊时,人的表现趋近于躁动不安的状态?
詹姆斯·丹克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回到格林森在50年代提出的焦躁型和冷淡型无聊,它实际上触及了无聊心理学研究中一个有关唤起(arousal)的重要争论,即无聊是一种高唤起水平还是低唤起水平的感觉。(注:唤起水平反映了感官受刺激后形成的觉察状态,个体在生理和心理上做出提高或降低反应水平的程度。当唤起水平升高,心跳、血压、警觉度和活动能力等上升。)科学家们不经常承认这一点,但我们都是带着个人偏见来的,不是吗?我的个人偏见是无聊的感觉就像焦躁——我坐立不安,踱来踱去,我不开心、不舒服,我想得到些什么,但想不出来我到底想做什么。对我来说,无聊就是这样。所以我从前一直认为无聊状态对应的是高唤起水平。
但我们在2018年做的一项研究,修正了这种偏见。我们让两组参与者报告自己感觉有多无聊,同时还让他们报告了焦躁不安和犯困的程度,这都发生在他们读故事的时候。“有趣故事组”的人读了《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和《福尔摩斯:红发俱乐部》的片段,这些应该能够吸引人。“无聊组”的故事则摘自《土壤的性质和特性的要素》和一本1966年出版的《古代的世界》。最终我们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在报告感到无聊时,不安的程度也增加了,更重要的是,困意也更加强烈。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他们既激动又有点昏昏欲睡。
在另一项目标类似的研究中,通过监测参与者的生理指标,我们再次验证了这种混合了躁动和倦怠的状态。在做那些无聊的任务时,参与者的皮质醇水平提高了,这是唤起水平提高、紧张感增加的标记。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进入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心跳会变缓,皮肤导电性会增强,也就是出汗。但我们的实验对象却出现了心跳加快、皮肤导电性下降的相反状态,这指向唤起水平的不足。
安德烈亚斯在他的文章中也梳理了这一系列事实,他的推论是,我们不该再把唤起作为无聊的定义的一部分。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我更想补充的是,这些实验告诉我们,无聊的确是一种在兴奋冲动和无精打采之间波动的状态。实际上,关于无聊,最关键的可能就是,这是一种波动过快的生理、心理体验——在短时间内经历过高和过低的峰值。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还没有测试过,这将是我们实验室未来几年要做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无聊和抑郁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性?
詹姆斯·丹克特:目前只有很少的证据显示,无聊是抑郁的先兆。表面上看,无聊与抑郁确实有很多类似的特征,几乎难以区分。但抑郁是由悲伤定义的,是一种无法感受到愉悦的状态,抑郁者会消极地评价自己。而我们已经明确,无聊的本质是我们想要寻求更有满足感的活动。抑郁和无聊的出现,都意味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出现了问题,甚至切断了联系,但抑郁让人责备自己不够好,而感觉无聊时,我们更多是对外界不满。
在这个问题上,我经常联想到系统动态平衡的机制,就像我们的身体可以通过排汗或者发抖来自行调节体温,让它稳定在一个平衡的范围内,我想我们很可能也需要一种认知功能的动态平衡,调节我们与世界的互动。如果互动程度过高,我们可能会体验躁狂、焦虑,如果过低,就会趋向抑郁,而无聊属于略低于平衡的值域。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想,还没有任何数据支持。但如果这是成立的,一个潜在的重要问题是,是什么让无聊转化成抑郁的?如果能够证实无聊是抑郁的一种原始形态,我们或许能更早介入,帮助更多人免受更严重的抑郁症。
三联生活周刊:除此之外,你认为还有哪些方面值得研究无聊的心理学家继续探索?
詹姆斯·丹克特:除了单调、意义缺失和注意力下降,还有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因素,可能导致无聊的体验。比如,最近有位学者针对高中学生做了调研,他将“控制”和“价值”划为学生判断一个作业是否无聊的标准。如果他们认为情况超出了自己的掌控,或者一份作业出于某种原因不值得自己去做,也就是说,太难或太容易的事情都可能是无聊的,所以“努力程度”是一个我们还不够了解的重要方面。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科学家们还希望继续从神经信号的角度研究无聊的动态过程,这是一个难点,因为任何一种情感体验,快乐、悲伤、恐惧,都不是静止存在于一个独立的时刻,而是随着时间演变的。如果我们能找到用于测量这个动态的神经信号,将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进展。

我们越来越觉得无聊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无聊透顶》中提到了一个“了不起的男人”,他在14年中每天要重复一个动作三四万次,确保金属条被准确送入钻孔机,但他依然觉得这份工作有趣,值得全神贯注。那么心理学家如何看待无聊感知的个体差异?无聊倾向性量表(Boredom Proneness Scale)是最权威的测量工具吗?
詹姆斯·丹克特:80年代末,法默(Farmer)和桑伯格(Sundberg)发明了无聊倾向性量表,这可能是无聊研究中至今使用最多的一个测量工具。当我们把无聊倾向性当作一种个体特质,只能说明一个人大致处于频谱的哪一端。我个人认为所有人都会感到无聊,但有的人能很快地处理,甚至不承认他们有过无聊的感觉,因为它消失得如此之快。而在频谱的另一端,有些人饱受无聊的日常困扰,无聊的感受更强烈,出现的次数更多。过去10年,在滑铁卢大学,我们收集了大概2000份无聊倾向性的数据,它们呈正态分布,也就是说,整体上约有15%的人需要和很高的无聊倾向性做斗争,而另有15%的人几乎不会感觉无聊。当然,研究者仍在不断改进、发明新的量表,但每种表都有它的局限性,也有心理学家从根本上质疑无聊倾向性这个概念。我希望人们意识到,这仍然是个有争议的概念。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我们花费在社交媒体、电子游戏、视频网站上的时间似乎越来越长,整体而言,是我们更容易无聊了吗?无聊会发展成一种公共卫生危机吗?
詹姆斯·丹克特:这是些很好的问题,但很难回答。如果我们想知道现在无聊是否比20年前更严重了,最好的方法是回访20年前测量过的人,对吗?但这真的很难做到。伊丽莎白·韦布莱特(Elizabeth Weybright)做过一些关于青少年与无聊的研究工作,非常有趣。从2007年开始,她调查了一群美国14~16岁青少年,同样的人跟踪了10年。数据基本上显示,无聊的情况是在加重的,现在比10年前更糟糕。但她并没有分析为什么会这样,数据还不足以支撑更广泛的结论。
最近几年,有一些中国学者发表了很好的研究,探讨无聊、心理健康和智能手机使用的关系。我不想做过于悲观的预言,但是根据数据,大概有4%~8%的人对手机的依赖程度接近成瘾,而这与更高水平的无聊、焦虑和抑郁相关。这是一个不小的百分比,但也不是所有人,所以我想这还不算是一种流行病。
我们在书中也谈到,我们在无聊时拿起手机玩《俄罗斯方块》《糖果传奇》,刷社交媒体,是想缓解无聊的感觉,而且效果确实很好,因为它们成功占据了闲置的注意力。在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社交媒体几乎拯救了我们,人们用抖音做了不少有意思的非常有创意的事。所以科技并不是一切问题的来源,关键在于我们是在主动还是被动地使用这些产品。
三联生活周刊:新冠疫情是否改变了有关无聊的讨论?如果有朋友问你,他的孩子或者他自己觉得非常无聊,你会给出什么建议?
詹姆斯·丹克特:我想疫情带来的改变是,人们现在开始注意到无聊这件事了,而在隔离生活之前,很多人可能会说,做完这件事,还有下一件事等着我,我没空觉得无聊。在新冠突然暂停原来的生活之后,无聊的感觉促使我们去思考,什么对自己是最重要的。
对于孩子的无聊,父母或许应该说,你需要自己面对这个问题。另一个办法是直接提供一些选择,你为什么不去玩会儿这个?但问题是,无聊的威胁作用在每个人的主动性上,其他人告诉你该如何行动是没用的。所以父母应该更直接地和孩子沟通,让他们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告诉他们,只有自己能帮助自己摆脱这种困境。
同样地,成年人也需要正视无聊的感觉,不要轻易向负面的情绪投降,否则很容易选择那些短视的、无法带来满足感的解决方案,比如一直刷手机,或者再多喝一杯酒。所以保持冷静是首要的。接着,可以试着做两种反思。第一,想一想为什么我会觉得无聊。有些流水线工人在重复单调的工作时,会每小时都给自己设定一些挑战,试图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这个办法有多么有效,但是重新定义眼前的任务,换种方式思考,应该是有益的。第二种反思是,问问自己,我有什么更长远的个人目标?这些目标可能一两年都无法实现,但每一次反思练习都在提醒我们自己最看重的价值。最后一个建议是我的合作者约翰常说的,去认真做事,这很像耐克的口号,去做事,你一定会熬过无聊的感觉。我也同意这种方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创造力和无聊之间是否有相关性?
詹姆斯·丹克特:有人喜欢说无聊会让你产生创造力,我完全不相信,也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有一些证据表明,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富于创造力的人,或者说你已经培养出了自己输出创造力的出口,当你感觉无聊,这个出口可以帮助到你。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的逻辑是,已有的创造能力可以扼杀无聊,但无聊不会让你更有创造力。
开拓创造力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什么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或者说是一个输出创造力的出口呢~任何艺术家,无论是作家、音乐家、雕塑家还是画家,他们会不断精进他们的手艺、实践,甚至每天练习,对吗?如果你没有花时间发展过你的创造性技能,创造力要从哪里来呢?做出这种区分真的很重要。我自己也有输出创造力的渠道。我从11岁就开始弹吉他,从14岁开始,就写了自己的歌,相比弹别人的歌,我就是更喜欢原创。我可能已经写了100多首歌曲,但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做,只是因为我想要这样。还有一点,我经常在感觉无聊的时候去弹吉他,但不是每次都能缓解不好的感觉,可能只有七八成的时间是奏效的。所以即使是已经培养出的创造力渠道,可能也不会解决无聊的困扰。所以我觉得不应该让大家产生错误的期待。为什么进行创造活动不是百分百有效的呢?我们还没有任何答案,因为很难进行研究。这就是我对于无聊和创造力的看法。
三联生活周刊:无聊是人类特有的体验吗?
詹姆斯·丹克特:我会担心从独特性的角度进行讨论。我们人类对这个星球的塑造作用的确是其他物种无法企及的,但我们在动物的世界中会看到很多无比奇妙的现象。我看过一个视频,在加勒比海,很多对半劈开的椰子壳落入海中,章鱼会收集它们,躲在其中,是一种捕食的埋伏手段。但章鱼有时会将两个壳一起带到坡顶,钻入其中,将它们合起,然后从坡上滚下来,并且重复了一次又一次,它只是在玩儿。蜜蜂的舞蹈是一种精妙的沟通语言,蚂蚁的社群协作也非常了不起,有太多这样的例子,都在提醒我们人类的智慧并没有多么特别。
但有一件事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其他动物像人类一样如此热衷于寻求意义?也许我们对于意义的痴迷是我们真正的独特之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仅执着地为那些与自己有关的小事赋予意义,还要为每件事都在更宏大的尺度上找到意义。这种执念会带来麻烦,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许多事就是琐碎的、不重要的,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社会不太能包容意义的缺位。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是被教育要学着做有意义的事。另一句经常听到的说法是:“只有无趣的人才会感觉无聊。”这些观念或许让我们更容易对无聊做出消极被动的反应。
詹姆斯·丹克特:是的,我赞同这种说法。无聊是无意义的信号,而我们如何回应无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时间的关系。即使在不同的文化中长大,现在的人们也都会看重自己是否多产,当我们做的事情不能带来效益,做不到就会感到愧疚。我想,我们最终必须改变这种感知时间的方式。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工作自动化,那些现代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比如律师、医生,完全可能被机器人取代。这并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但我相信,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身与时间和生产力的关系。
(实习记者/张宇琦)
文章作者


张宇琦
发表文章0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44人
《三联生活周刊》实习记者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