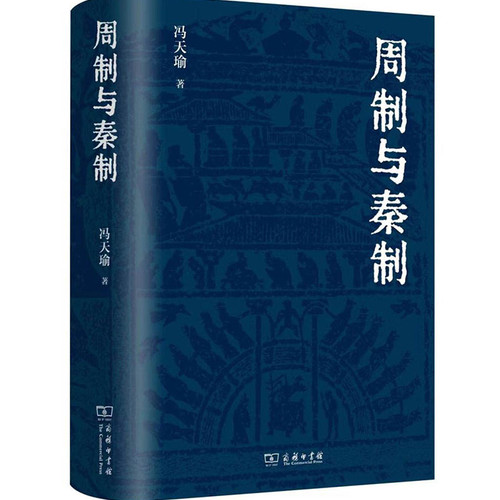人,还能诗意地栖居吗?
作者:维舟
2022-11-15·阅读时长6分钟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写道:“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常被误解为是对某种“诗意生活”的追求,但哲学家海德格尔给了它全新的阐释:现代社会诸神退散,工业文明对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人还是人,“劳绩”更甚,但“诗意”和“大地”恐怕都已远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在美好的过往不可重现时,如何“诗意地栖居”已成为一个生存哲学命题。
也就是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其实是工业时代的人对一种失落理想的追怀,也正是因为技术的发展把人们带出了依赖于大地的生存,才让现代人过着无根的贫瘠生活,我们似乎是被抛入一种自身无法选择、快速变动又没有特色的处境里,人的内在本性、文化深度都不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看似忙忙碌碌,但他既难以找到生活的意义,甚至也无法感受到自身的完整性。
作为海德格尔学派最当红的哲学明星,韩炳哲的著作虽然涉及广泛的社会议题,但始终聚焦于一点,那就是:后现代社会里人的生存处境,并在这种病理诊断的基础上开辟可能性。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会面对不同的问题:当一个时代的“舞台背景”发生变动时,即便是同一个问题,也会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意味,需要全新的反思。
可以说,自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现代社会始终处于持久的精神危机之中。在此之前,“人”的定义和处境,实际上都是在他/她与神的相对关系中得到理解的,然而在那之后,原先那个起到“锚定”作用的绝对价值消失了,人所面对的是一个由技术、资本和权力所组成的无机世界。表面上看,人取代了神的位置,但现代历史证明,人类不仅难以扮演好这个新角色,并且更糟糕的是,我们日益无法理解自身的处境。

这种技术时代的存在困境,海德格尔、本雅明和阿伦特等人也早有触及,但韩炳哲则把握到了后现代社会的不同:技术不再只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异化力量,而变得更加隐蔽。置身于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并不只是彼此孤立且被动地屈从于外部强迫,恰恰相反,他们是通过彼此交流的“超交际”,不知羞耻地暴露隐私来获得关注,由此通过自我展示和自己揭露,参与到数字化全景监狱的建造和运营之中(《透明社会》)。
不知不觉中,诱导、说服已取代了强制,成为新的异化力量,它看起来没有那么粗暴、冷酷,但却更难对付了。暴力并没有消失,但它“从可见转为无形,从正面直击转为病毒性感染,从粗野蛮横转为沉思内省,从真实转为虚拟,从生理转为心理,从消极排斥转为积极扩张,并且回到皮下、交际之下、毛细结构和神经元的领域,以致产生‘暴力消失了’这样的错误印象”(《暴力拓扑学》)。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是一个“绩效主体”,被驱使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取成就,这伴随着一种虚假的自由感,似乎其所作所为都是自愿做出的,但结果其实是自由与强制合而为一,连“自由”的边界和内涵也变得前所未有地模糊。
在这种情况下,“娱乐”也早已不再像工业时代那样,是一种工作之余的休闲消遣活动,而可能无所不在地侵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让人无法区分“真实的现实”和“虚构的现实”,成为一种观看、理解社会现实并生活在其中的新范式,因为“现实本身似乎就是娱乐的结果”(《娱乐何为》)。工作/休闲的二元对立已不复存在,两者日渐混同,在创新经济的领域里,连工作也常常是在“玩”,很多人因此产生一种致命的错觉:娱乐就是生活本身。
当高贵与平庸混同,在一派喜气洋洋的严肃之中,世俗化的现代生活已经没有神圣性可言,美作为最后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其庄严性已被抽空,成为任何人都可以消费的廉价物品,“美被磨平,变成了被喜欢、被点赞的对象,成了随意和舒适的代名词”(《美的救赎》)。这是一个同质化的时代,哪怕原本对立的存在,现在似乎也没有质的分别,而只有量的差异,“数字化的无差别性消除了切近与疏远的所有表现形式”,也“使世界失去其光芒和神秘属性”(《他者的消失》),随着距离的消失,崇高感、神圣性和超越性也随之消失,人们对他者茫然无睹,在自恋的纠缠中深陷于抑郁而不自知,还误以为这是一段兴奋的体验。
韩炳哲的论著已点明了后现代社会中人的困境:原本清晰的边界已变得模糊渗透,乍看起来强制性的力量已消失不见,但原有的结构仍然存在,只是以更隐蔽、更难对付的形式存在,人们既无所遁逃又无法抵挡诱惑,到头来连抵抗的意志都消失了,陷入一种“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的无意识抑郁之中。这样一个丧失超越性追求,而只满足于浅薄世俗欲望的人,就是尼采所说的“末人”,是人的高贵性和神圣性的失落,意味着一个可怕的前景:人可能主动放弃“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这些问题为什么重要?那就需要我们回到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去理解了。
在文艺复兴时代,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的解放”,这意味着反对中世纪那种让人屈从于神的状态,为人赋予尊严,而这往往伴随着一种自我力量感的增长和对未来不断进步的信念。然而,正如有西谚所说的,“当你怀抱理想的时候,小心它实现的那一天”——当人们取代神灵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时,等来的并不是彻底解放,相反,却是前所未有的自我奴役和无意义感。
虽然这看似让人绝望,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强烈的主体性,本身就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实际上,一个传统时代的人,即便在事实上过着田园生活,但他不大可能像现代人这样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去追求“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用哲学的语言来说,他/她可能是“自在的”,却不是“自觉的”。
这就像是一个“失乐园”的过程:只有在失去之后,我们才能懂得自己失去的究竟是什么;也只有理解了当下的处境,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生而为人所应当过、值得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又如何去实现它。
现代社会中的很多人是不考虑未来,只活在当下的——当每一天都像是在重复前一天时,那明天也不值得期待了,但与此同时,正因为明天可能就没有明天了,所以才要过好每一天。世俗的中国人对此并不陌生:和现代人一样,中国人普遍不关心未来的审判和救赎,因而“过日子”对中国百姓具有存在论的意义,所谓“平平淡淡就是真”,人们正是在这样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完成自我救赎。
的确,现代社会出现一种“恐怖的同质化”,然而,后工业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也恰恰是“独异性社会”,格外突出每个人的独特性。这意味着一种“自反性现代性”的出现:人们察觉到,现代社会本身已经成了问题的对象,因此,如何既突出自身的主体性,又将自己作为客体来进行反思、调整,就变得尤为重要。
这种反思性本身也贯穿于韩炳哲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太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他那种“格言式长句”的写作风格倒是更接近齐格蒙特·鲍曼那样的社会学家,关注的领域也横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但始终聚焦于“人的处境”这一根本性的主题,致力于回答人们最关切的问题——他在意的并不是总结出时间坐标轴中的“发展规律”和“结构”,而是在共时性的空间中上演的无数“现象”。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哲学家”常常是某种脱离现实生活来进行抽象思维活动的形象,但实际上,一个好的学者势必是对最前沿的时代变动有着敏锐感知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这种现实关怀,就难以激发理论创新。恐怕正是这种对后现代社会现实的深切洞察,才使得韩炳哲的论述激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和思考——他的“走红”,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介入现实”的成功回应。
这也是我们需要思索的另一个问题:在一个科技和商业主导的时代,哲学还能做什么?19世纪末以来,人文精神在一个日渐技术化、商业化的世界里渐渐衰微——尤其是哲学,它原本正因不牵涉实用技术而被视为高等教育的王冠,到后来却因为这一点而被看作无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恰恰因此,才使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我意识,在普遍的精神危机中重新理解了自己所应承担的使命,那就是:认识人的生存处境,并在反思中促使所有人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文章作者


维舟
发表文章32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417人
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